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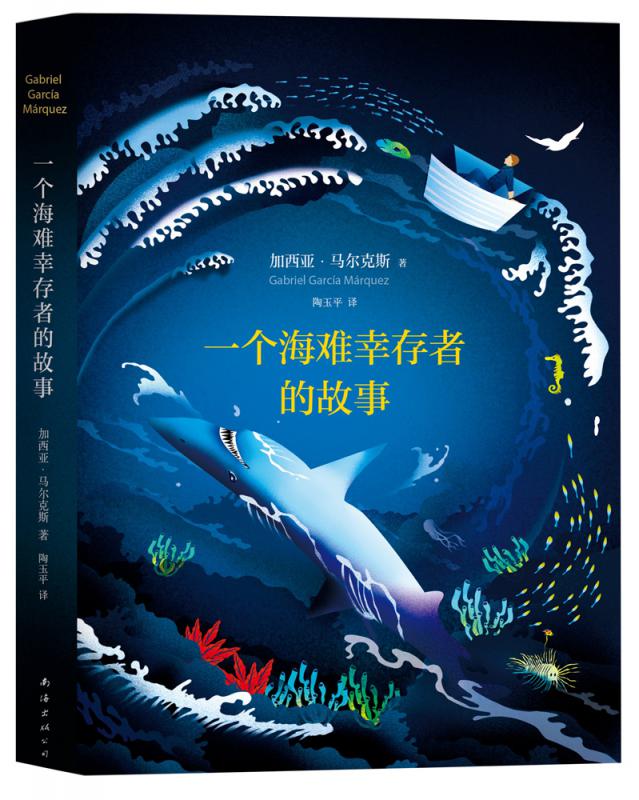
圖:加西亞.馬爾克斯著作、中譯本《一個海難幸存者的故事》由南海出版公司於今年六月出版\資料圖片
魔幻與現實都是人心的投影,人心的惡若沒有邊界,就會放縱出無限黑暗。讀馬爾克斯(港譯:馬奎斯)的作品會令人分不出何為虛幻、何為真實,很多經典的片斷會在人的腦海中久久迴旋。他用魔幻的筆法代替了主人公心靈的旁白,將所有要訴說的化成了種種奇幻的景象,讓讀者用心填補語言的空白。
習慣了老馬的魔幻現實,但你知道他還是一位傑出的新聞記者嗎?一九五四年,他曾通過深入調查取證,報道了哥倫比亞麥德林市的一個城區惡性地面坍塌事件,新聞報道直指政府管理上的疏忽。在一九五五年,他又通過細緻的採訪,以新聞連載的形式揭穿了哥倫比亞皮尼利亞專制時期,一則被當局美化的海難醜聞。兩次報道,前一次將馬爾克斯推上了明星記者的紅毯,而後一次,則開啟了馬爾克斯流亡的旅程。
《一個海難幸存者的故事》,便是那則海難新聞連載的結集,報道的真實性得到了主人公當年同艦上海軍戰友的照片證實。書中,貝拉斯科那些魂歸大海的夥伴們的聲音似乎仍在海面上迴盪,那個始終保持着整潔形象的一級士官胡里奧、興奮的等待歸家的小海豹薩博加爾、「想看我暈船,那得整個大海都暈了才行」的十全十美的海兵任希弗的形象栩栩如生。
海難幸存者貝拉斯科在飄流筏上的十天十夜,同樣被寫得層次分明,每一天、每一夜,在作者筆下都是充滿變化,不論是幻聽、幻視、幻覺,還是身體承受的痛楚,以及內心的孤獨、恐懼,都以十足的畫面感呈現在讀者面前。鯊魚的背鰭仿若依舊在水面上逡巡,海浪搖晃中的皮筏似乎依舊在孤獨地隨波逐流。
不論馬爾克斯把貝拉斯科的海上「飄流記」寫得如何生動,佔了全書怎樣的篇幅,但馬爾克斯的醉翁之意顯然不在於此,本書的核心命題只有一個,那便是揭露皮尼利亞當局對那次海難事故的故意美化,還原事情的真相。原來,出事的當天並沒有當局口中說的暴風雨,只是一陣風使超載的軍艦發生了傾斜,導致胡亂堆放在甲板上的走私貨滾落大海,連帶八名船員落海,艦方未能採取任何措施救援落水者。即使是在救生筏上,也沒有任何必備的用品。
當「好運氣」的貝拉斯科奄奄一息地出現在哥倫比亞北部的一處荒僻海灘上,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禮遇」,住院期間受到了軍方嚴密地「保護」,只能接觸官方記者,他被精心「打扮」成了一位英雄,授予了他民族英雄稱號,得到了選美皇后的獻吻,成了多種商品的代言人,為此他甚至發了一筆小財。這樣的日子無疑很「享受」,萬眾矚目,財源滾滾。貝拉斯科突然活成了一個連他自己都不認識的人,一個政府偽造的英雄,一枚軍方的政治「棋子」。然而「好景不常」,英雄很快過氣,不久他便被軍方遺棄……
假如貝拉斯科沒有從「被英雄」再到「被遺棄」的過山車式的歷程,也許他就不會自己主動跑到報社來問他的故事能賣多少錢。不論貝拉斯科將真相和盤托出的目的如何,他為了這次講述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遭遇種種威脅利誘,被迫離開了海軍……馬爾克斯稱他為英雄,但原因並不是他在海上飄流了十天十夜,也不是他的講述,而是他對這篇還原事實真相,卻給他帶來厄運的記述,沒有否定一個字。
這是出於良知嗎?是出於被軍方遺棄的報復嗎?還是由於生活無着,在慌不擇路時鋌而走險選擇的生財之道?答案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真相已然公諸於世。
全書不足十萬字,書中沒有大場面的鋪排描寫,沒有人物在政治立場上的心靈獨白,也沒有對於逝去戰友的煽情緬懷,更沒有對當局的直接抨擊批判,全書行文簡單、乾淨、利落,但讀者恰恰能在這些「缺失」、「留白」之處,看到最深摯的戰友情、看到海上的孤膽英雄貝拉斯科,看到獨裁當局的專橫、虛偽,玩弄事實的真相,以及如何操控媒體,打壓異己。
貝拉斯科的海軍生涯是荒誕的,馬爾克斯的記者生涯同樣是荒誕的,現實一旦荒誕起來,比小說更令人瞠目結舌。該書最成功之處便在馬爾克斯在寫與不寫之間的虛實掩映與分寸拿捏,那些沒有直接見諸筆端的內容,反而成了全書的亮點。它們隱藏於字裏行間,仿若是從馬爾克斯的筆鋒處種下的種子,經文字與情感的呼喚養育,再重新在讀者的心中生長出來,顯現出強大的生命力。
如果說新聞給了馬爾克斯無限接近於事實真相的空間,那麼魔幻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無疑又給了馬爾克斯進一步重構現實,再現現實的另一重路徑。不論表現形式如何,馬爾克斯的留白式寫法,都為其作品增添了厚重的魅力,延展了文字本身的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