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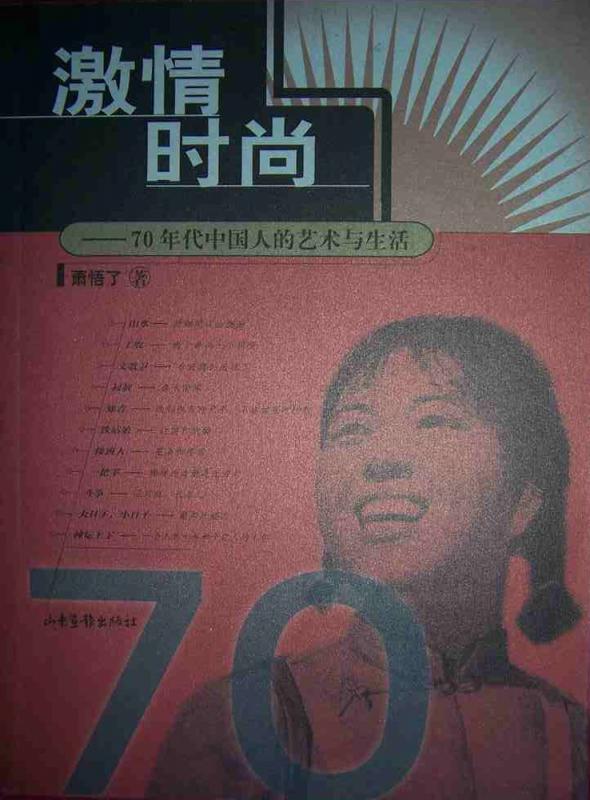
圖:《激情時尚》封面\網絡圖片
一直對繪畫有很大的興趣,看到《激情時尚—70年代中國人的藝術與生活》便將它買了下來。隨手翻來,一幅幅熟悉的繪畫呈現在眼前,彷彿被一隻手揭開了心淵處的封條,於是,塵埃輕輕地飛揚,露出了有些模糊泛黃的記憶。
《激情時尚》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繪畫作品集,幾乎彙集了「文革」中後期的繪畫精品。它們出自一批充滿革命激情和純真信仰的藝術家的筆下,如今他們許多人已去世,或年至耄耋,也有的成為畫壇領軍人物,甚至巨擘。而正是他們讓我在不講藝術的年代,領略到藝術的魅力。
上世紀七十年代,畫冊少得可憐,而且絕大多數是黑白的。因此,看過的畫冊便有了不可磨滅的印象。記憶中,當時看過的畫冊僅有兩本,一本是列平─現在譯為列賓─畫冊,《伏爾加河縴夫》、《不期而至》、《伊凡雷帝殺子》等作品便從那本畫冊中看到的。我被列賓深深地震撼了,而且至今對俄羅斯巡迴展覽畫派那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情有獨鍾,即使後來有人說巡迴展覽畫派的藝術成就在世界繪畫史遠不及印象派等現代派的成就大,我卻始終認為巡迴展覽畫派不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在世界繪畫史上都是不可替代的。另一本畫冊名字忘了,是囊括了古元、彥涵、李樺等中國第一批木刻家的木刻集。兩本畫冊都是銅版紙印刷,在當時算是很精美的了。
除了那兩本畫冊,當時,少不更事的我還總是為滿街的漫畫樂不可支,出於對繪畫的酷愛,我對所有的圖形充滿了興趣。在那個一切為政治服務的歲月裏,革命浪潮一浪推一浪,漫畫作為一種快捷的表達方式,充斥於我們生活的各個角落,我也就時常有機會當街臨摹路邊懸掛的各種漫畫。批判修正主義時,臨摹過赫魯曉夫、柯西金之流的醜態;批林批孔時,臨摹過林禿子、孔老二的嘴臉……那時,條件簡陋,買支繪圖鉛筆都算奢侈,我只是一個破夾子,夾上幾張破紙,那紙多是廢舊油印材料的背面。可惜了,那些珍貴的藝術臨摹品早已盡失。
對繪畫的熱愛,使我還非常關注當時報刊上發表的每一幅繪畫作品。任何時代都需要符合其時代的主流作品,只是沒有一個時代像「文革」那樣完全剔除了主流之外的一切東西。也許正是由於排除了主流之外的一切作品,「文革」中繪畫作品的數量稀少,其中的優秀作品自然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因此,畫集裏的一幅幅作品常常如老友,在我心中激起一種懷舊的情緒。
我總覺得幾代人之後,當這段歷史對他們已經成為遙遠的過去,他們沒有經歷過煉獄般的心靈拷問,也沒有感受過切膚的傷痛,而只靠史料去認識這段歷史,就如同我們今人讀秦始皇,讀康熙、乾隆。那時,他們會以平和的心態品味這些作品,他們會從中讀到許多可愛的東西。有些作品可能表現出幼稚滑稽,甚至愚昧的偏執,但更多的是單純、樸實、真誠的激情。
任何藝術品都是作者對自己的思想意識,或是對社會理解程度的圖解。上世紀七十年代因為它歷史的特殊性,使作者自己的思想意識高度統一在外部的控制之下。但是,隨着時間的流逝,優秀的作品,會淡化它的時代背景,呈現出作者在不自覺中賦予作品的人性。
《激情時尚》畫集裏,陳衍寧的《海港新醫》中女赤腳醫生的溫厚靦腆,湯小銘的《女委員》中女委員的純樸幹練,潘嘉峻的《我是海燕》中女電話兵的勇敢無畏,楊之光的《礦山新兵》中青年女礦工身上洋溢的那種青春氣息,在那個年代的作品中都是優秀的。至於畫中的她們的豐滿,是那個時代的審美標準,環肥燕瘦,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審美標準,這不足為奇。
去除那些作品中極富政治性的表現形式,人性仍然隨處可見。《針麻創奇跡》如果僅從一個手術場面來說,無法否認它表現出了靜謐、緊張、認真的氣氛,準確地體現出醫生救死扶傷的職業精神。而畫集中,許多描繪領袖的作品也都表現得親切、平易、樸實,自然地流露出一種人性的美。
雖然,那些作品都是政治運動的產物,但還是反映了人們對美好的品德、行為、事物,及人們內心中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生在一個怎樣的時代是人們無法左右的,但並不能說生不逢時,每一個時代會有自己的烙印,但也必定會有人性共通的痕跡。其實,藝術很難完全脫離政治,古典主義畫家大衛的《馬拉之死》、浪漫主義畫家德拉克羅瓦的《自由引導人民》、西班牙畫家戈雅的《法國士兵槍殺西班牙起義者》都是政治,俄羅斯的巡迴展覽畫派的作品更是充滿政治色彩,即使看上去與政治最遠的印象派也是對正統學院派的反抗和挑戰。也許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作品因為完全服務於政治而變得膚淺,但由於那些藝術家們懷有飽滿的激情和純真的信仰,從而用自己的筆為歷史留下了一個時代的足跡、一個時代的經典。
其實,書名《激情時尚》,「時尚」一詞用在這裏有些輕佻,卻顯示出今日人們已經開始對那段歷史有了平和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