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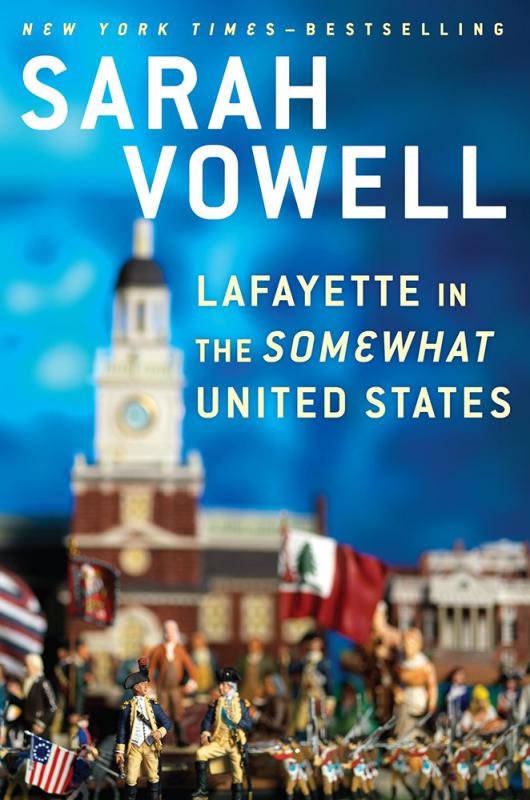
圖:美國暢銷書作家福威爾(Sarah Vowell)及其作品《Lafayette in the Somewhat United States》 資料圖片
一八二四年八月十六日,法國貴族拉法耶特侯爵飄洋過海,重返紐約,那時離他參加美國獨立戰爭已過去了三十年。八萬紐約客,也就是全市三分之二的人口,聚集到港口歡迎他。之後一年內,他訪問了當時美國所有的二十四州,每到一處萬人空巷,群眾夾道歡迎。一九三四年,他逝世一百周年之際,國會兩黨又罕見地達成一致,通過決議,和總統羅斯福一起讚揚他為「美國的朋友、華盛頓總統的朋友、自由之友」。即便是現在,在美國各地也隨處都能發現以他命名的地名。
美國人為什麼對拉法耶特青睞有加?自封「兼職歷史學家」的美國暢銷書作家福威爾(Sarah Vowell)在《拉法耶特在多多少少統一了的美國》(Lafayette in the Somewhat United States)中評價說,這是因為他屬於美國獨立戰爭一代,曾是「國父」華盛頓、傑佛遜等人的好友,但既不屬於北方,也不屬於南方,非共和黨,也非民主黨。在國父一代凋零殆盡,總統競選爭議巨大,南北各州對黑奴制度爭論不休的歷史時刻,他成為獨立戰爭光輝歷史的活豐碑,讓美國人得以緬懷前輩的犧牲,自誇立國的理念。
福威爾擅長在一本正經的正史之外找到被傳統歷史學家忽略不計的笑點。她將參加獨立戰爭時才十九歲的拉法耶特描述為「渴求榮譽,憎恨英國」,少不更事的貴族小青年。他被任命為北美殖民軍將軍時並無一兵一卒,而且第一次戰鬥就小腿受傷。為突出拉法耶特重訪美國大受歡迎的盛況,她又作了這樣的比較:一九六四年「披頭士」到紐約,當時人口七百萬的國際大都市只有四千人來迎接這個聞名世界的英國搖滾樂隊。她也讓美國的國父們走下神壇,展示了他們的人性弱點:嫉妒,易怒,小肚雞腸等。她甚至猜測他們在黑奴制度上的嚴重分歧不是因為政見有多不同,而要歸因於當年新成立的大陸議會成員被英國軍隊追捕,狼狽逃出費城,被迫在約克小鎮同宿幾夜,同伴的深夜呼嚕讓他們刻骨銘心。
不過,作者的搞笑「畫外音」並不意味着她不理解歷史的嚴肅性。她曝光法國國王路易十六支持美國獨立戰爭,為殖民軍提供慷慨的經濟資助,卻忽略了國內飢寒交迫的憤怒民眾,乃至若干年後在法國大革命中丟了腦袋。拉法耶特也不是完人。他拋妻別子,不顧家庭來到美洲大陸,盛讚所到之處,美國人如何淳樸友好,福威爾點評:「只有白種男人才會那麼評價」,暗指美國社會一直存在的種族、性別不平等。
無論專業還是業餘,以古喻今、借古諷今大概是所有歷史學家都免不了的習慣。福威爾描述在獨立戰爭的曼穆士(Manmouth)戰役中,華盛頓痛罵怯弱的李將軍(Charles Lee),把他趕到軍隊後方。她起初疑惑為什麼現在的「李子關」(Fort Lee)會以懦夫之名命名,之後恍然大悟:原來這是新澤西共和黨州長克里斯蒂利用職權,讓手下製造橋樑擁堵,藉以報復某民主黨市長的地方。正如當年李將軍在李子關臉面掃地,克里斯蒂的聲譽也因之一落千丈,從領先共和黨內的總統競選落魄到被振出局。
更發人深省的是,書中談到二○一三年國會中的「茶黨」極右分子以政府財政預算為要挾,希望通過迫使政府停工來實行自己的主張。作者點評:正如十九世紀法國人空有革命激情卻缺乏自治經驗,造成血腥鎮壓氾濫,美國國會中的新人毫無談判、妥協的經驗卻意氣風發要辦大事,失敗早就注定。
特朗普政府上台百日餘,從蔑視專家,亂發政令,舉步維艱,發展到吸取教訓,諮詢專家,學會妥協。歷史與現實有時驚人地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