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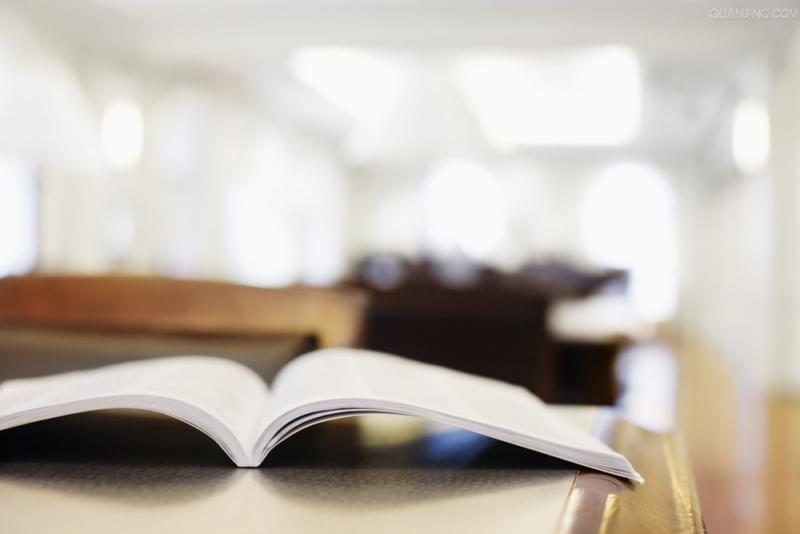
一個人一生中總會碰到幾個好的老師,也說不定會碰上幾個不好的老師。不好的老師都是相似的,好的老師各有各的好。
小學四年級,班上來了一個新的語文老師,姓陳,名孔金。他是復員軍人,原先在部隊文工團吹奏單簧管。一張紅撲撲的臉,中短身材,因為不是本地人,通常說普通話,在我們學校,是一個很另類的老師。
我們那時都土得掉渣,哪裏知道什麼單簧管,陳老師在學校早操時,就吹奏他的單簧管,為我們的做操伴奏。那是一支黑膠管為主體的樂器,黑管上打了好多孔洞,用一些金屬的按鈕操作,有的孔洞按住,有的放開,黑管就發出不同的聲音,組成不同旋律。
那支單簧管可以分解成三節,收藏在一個很精緻的黑盒子裏,用的時候旋上,陳老師含住簧片那頭,用舌頭舔舔它,可以吹出悅耳的樂音。
陳老師教語文,按部就班,講課時雜以很多手勢,課餘很熱衷地在同學中傳播他的音樂常識。他挑選了幾個同學,教我們看簡譜,教我們吹笛子、拉二胡。那年頭大家經濟條件都不好,笛子最便宜,又最容易學,因此我們班上至少有十個八個同學都學會吹笛子。
後來學校早操時,上台伴奏的就不只是陳老師的單簧管,還有幾個勉強叫做會吹笛子的同學。學校當局的寬容,激勵了這些孩子的上進心,他們覺得自己和別人不一樣,他們多了一種本事,可以和老師平起平坐,可以憑自己小小的本事,去幫助其他人。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家鄉各處也建起小高爐大煉鋼鐵,傍晚我們集合出發,沿街行進,每人手上一支笛子,整齊地吹出一些雄赳赳氣昂昂的旋律。街道兩旁的人家,都有人探頭出來看我們這支奇怪的隊伍,一些十來歲的孩子,興致勃勃用稚拙的技巧演奏雄壯的歌曲,在風起雲湧的年代,宣泄少年的激情。
後來我們走到煉鐵工地,那裏小高爐高高低低,爐裏火光熊熊,工地上的人各自埋頭一本正經地為「超英趕美」盡力,我們站在一旁,用手上的笛子為他們吹奏鼓勁。空地上晚風掠過,鼻端有燒柴的焦味,笛音在空曠的山坡上被風一吹,霎時散於無形,但我們那時都覺得自己在做一件大事。
陳老師應該是「文革」前結婚的,他的妻子身材修長,容貌端莊,是好人家的女兒,可惜的是,她父親在解放初期被當作反革命鎮壓了。按理,一個復員軍人,是不應該與「鎮壓家屬」結婚的,陳老師為自己喜歡的女子冒了很大的政治風險,因此他在我心目中,更是一個非一般的老師。
陳老師如何教我語文,都沒有印象了,但我的音樂感覺,毫無疑問是他開啟出來的,因為他,我一輩子從各種音樂中得益良多。在很多孤獨、陰暗、幾近絕望的日子裏,音樂讓我得嘗人生的美意,讓我紓緩內心的焦慮,保持對未來的信心。
小學六年級時,班上來了另一位老師,也是教語文,也姓陳。陳啟漢老師天生駝背,前胸鼓起,後背隆然,因為駝背,他個子顯得很小,手顯得很長,不知是不是為平衡身體,他走起路來有一點八字腳。他整張臉三尖八角,鼻子是尖的,下巴也是尖的,兩個小眼睛精光閃閃,是他臉上最生動的部位。
一個駝背的老師,在同學間不免成為笑料,但陳老師永遠坦然。他上課很生動,喜歡用特別的比喻來說事情,那些比喻用閩南話說出來,更有一種帶泥土味的促狹,因為這一點頗得同學歡心,他慢慢地得到我們認同。
後來我們知道,陳老師是鎮上文藝表演的活躍分子,有時他在上課時,會忍不住在教室裏走台步,或一時興起,就扭起秧歌來。這種活潑的課室風氣,又使得我們的語文課,充滿生活氣息和過癮的心情。
按理,一個天生殘障的人,內心難免對人世有種種抱怨,他從小會受人欺侮,不容易交到知心朋友,他會有嚴重的自卑感,習慣遠離人群,用陰暗委屈的心情去看待人生。但陳老師永遠不缺笑容,不缺對平凡生活的熱情,教書之外,聽說他每晚都在鎮上的表演團體裏排練,然後有一天,我終於看見他登台。他飾演一個花花公子,在台上大耍功架,模仿喝醉了酒顛躓的腳步,大搖大擺腆起假裝的大肚皮,他的表演惹得觀眾席上此起彼伏的掌聲。
陳啟漢老師如何教我語文,我也都忘記了,但我記得他那種樂天開朗的性格,那種對厄運臨頭泰然自在的沉着。對於人間苦難,他有豁達的心胸去承受,對於藝術,他用全身心去擁抱。
那時我們多幼稚啊,我們的心智與人格都在朦朧狀態中,我們都在找人生的路標,悄悄從我們敬仰的人身上,去追慕那些讓人警醒、讓人欽羨的品格。兩位陳老師無疑塑造了我部分的人格,那比起課堂上的知識傳播,對我的一生影響更深遠。
高中時我的語文老師也姓陳,名文淡,他真是一個很淡很淡的人,淡到我們有時都不覺他的存在。
陳文淡老師也是外地人,也講普通話,花白頭髮,一張灰撲撲的臉。臉上長年有謙厚的微笑,小小眼睛裏潛藏一種不自在的膽怯,即使與我們打交道,他也總是有點擔驚受怕的表情。
陳老師教語文,有事則長,無事則短,他做班主任,也是奉行放任政策,有事稟過,無事退朝。那時我們每周有兩次作文課,每次兩節,陳老師的政策是:一次作文由他命題,由他批閱;另一次作文由同學自由命題,由同學小組批閱。這樣的政策大大開發了同學寫作的自覺性,讓我們感覺作文不是寫給老師看的,是寫給同學看的,是寫給自己看的。
每個班級都有兩塊大黑板,前面的黑板給老師板書,後面的黑板讓同學辦黑板報,我們自己便辦了一份報紙,每月更新,宣傳股約稿,大家商議排版,書法基礎好的抄寫。有一段時間,為了吸引同學目光,我們模仿五四年代《新青年》上錢玄同和劉半農「唱雙簧」的伎倆,捉一個話題,搬兩個觀點打筆仗,搞了幾期「百家爭鳴」,陳老師來看我們的爭論,手摸着下巴,眼裏有笑意,看完了揚長而去,不給一句評語。
平地一聲雷,「文革」來了。我們忙着造反,早已忘記有個陳老師存在。因為為人低調,陳老師是極少數沒有大字報的老師,但有時在路上遇見他,他總是有點惶惶然,眼神閃縮,挨着牆邊走,好像和我們打個招呼都有惡果。運動轟轟烈烈,誰也顧不上他,突然有一天,晴天霹靂,有同學跑來報信,說陳老師跳井自殺了。我們都往教師宿舍跑去,工作組在路口用繩子攔着,我們擠在旁邊,看遠遠的水井那邊有人在打撈。
後來陳老師給抬出來了,身體深陷在一個裝水果的木箱子裏,他的脖子扭曲成一個不可能的角度,頭髮披散下來蓋着半張臉,箱子太小,兩隻腳垂在箱子外面,一隻腳上的鞋掉了,腳板蒼白瘦削,另一隻腳上還套着一隻破舊的皮鞋,鞋跟磨損得歪了一邊。箱子抬過,紅磚地上留下一溜水跡,不知為什麼,看上去像血。
後來工作組派人往水井裏撒了很多石灰,據說是消毒,我心想,你們有誰比他更乾淨呢!
其實陳老師並沒有犯下什麼滔天罪行,他只不過曾經在大學裏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做過一個小小的負責人。他只是膽子小,永遠覺得自己有罪,永遠覺得自己有說不清楚的黑暗歷史,他被自己的歷史壓垮了,被泛政治的社會生活逼上絕路。
人說「陳林半天下」,我生命中居然有三個陳老師,他們教我語文,但更教我做人。如果我不做編輯,最想做的也是老師,一個好老師,塑造了眾多學生的人格,他們是傳道人,是提燈者,是像父親一樣的,有血脈在我身體裏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