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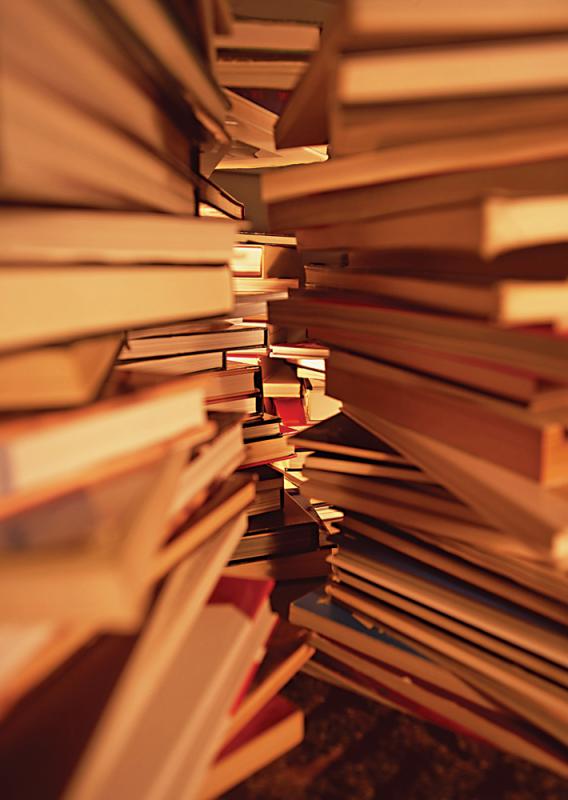
「我這裏有幾本書你可能會感興趣,有空來看看?」歷史系一位專攻東亞近現代史的老太太給我發了個郵件。她在這所大學執教三十五年後今年退休,正在清空辦公室。我應邀前往,她往身後一指:「那兩個架子上的書我都不要了,你隨便選吧。」走過去略掃了一眼,問她:「我都拿走可以嗎?」於是,剛開始說的「幾本書」變成了滿滿十三箱,一個助教幫我用手推車從她的辦公室到我的辦公室推了三趟,我倆都一身汗。
老太太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哥倫比亞大學讀中國近現代史,七十年代去台灣搜集博士論文資料,內地開放後又去進修、旅行過。半個世紀從各地零星搜集來的大批藏書,包括朋友、同事、作者送的,自己在書店買的,在圖書館清貨時買的,郵購的,網購的……若干人的點滴匯聚,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捆紮、打包、郵寄,至少半數都在我出生前就伴她教學、研究,如今瞬間都轉入我手中。我在辦公室清理出一個兩米高的大書架,將十三箱書略作分類然後上架。擺不下,沿牆又堆起齊腰高的四座書山。一看表,三個小時悄然溜走。
一共多少本?數了兩次都中途放棄。太多了。宋史清史鴉片戰爭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國民黨史共產黨史長征延安抗日大躍進「文革」改革開放。台灣史香港史明代以來中西交流史外國人與中國革命。日本通史現當代日本政治文化經濟農村生活。作者的名字好些耳熟能詳:張光直、黃仁宇、Marcel Granet(葛蘭言)、John Fairbank(費正清)、Jonathan Spence(史景遷)、Arthur Wright(芮沃壽)、Edgar Snow、Edwin Reischauer。還有中國文學英譯本:《紅樓夢》,林太乙翻譯的《鏡花緣》,魯迅謝冰瑩巴金茅盾沈從文老舍余華……數不過來。記得周一良先生八十年代中期參觀東京大學後說過,搜求專家學者長期積累的藏書,是建立專業圖書館的重要途徑之一。東大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館的中文藏書,就是從倉石武四郎、長澤規矩也等中國學學者的藏書發展起來的。我剛入手的這十三箱書,也足有一個小型專門圖書館的分量了。
還有好些匪夷所思的書,時過境遷,隨便翻翻都有趣極了。有本巴掌大的小冊子On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Double-Dealer Chou Yang , 一百零六頁,是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的英譯本。姚文元1967年寫的,北京外文出版社當年就翻譯了出來。這種文章居然還有英譯!譯給誰看呢?幫助工農兵學外語?向世界宣傳「革命形勢」?一茬茬潮頭浪尖的人物都退出了歷史舞台,作者和那個年代奇妙的一套語言都早被遺忘,這小冊子卻惚兮恍兮,飄洋過海,像五十年前廢墟中飄出的一隻蝴蝶的影子,最後棲息在我書架上的一隅。
另外一個巴掌大的小冊子,A Pocket Guide to China,是美國政府1944年為去中國參加抗日戰爭的美國軍事人員編寫的。編者對讀者(美國軍官和士兵)說,中美的共同敵人是日本;現在你要去中國,與中國人並肩抗日了,美軍在全世界最重要的任務莫過於此;可是你不懂中國人的語言,也不了解中國人,怎麼辦?所以小書的第二頁就有八個醒目的紅色漢字:「入境問禁,入國問俗」,配以英譯:「When you enter a neighborhood, ask what is forbidden. When you enter a country, ask what the customs are.」六十四頁的篇幅簡介了中國地理、中國人的風俗和「面子」,中日戰爭情況和中國軍隊的策略,還有漢語常用語、錢幣及度量衡轉換等實用信息。插圖裏的中國男人穿長衫、戴瓜皮小帽,齜着齙牙;女人身着旗袍,腰肢纖細。此書特別提醒:別看中國女性參加游擊隊和男人一起打仗(美國女性做不到),但對異性的搭訕,她們並不像美國女人那麼開放,所以輕薄不得。「你就是美國的使者」,編者提醒,別損害美國在中國人心中的美好形象。為了消除陌生和隔閡,編者費了不少筆墨說明中美兩國其實非常相似,乃至有這樣的話:「Of all the peoples of Asia, the Chinese are most like Americans.」七十年過去了,中美兩國在敵友的角色間不斷轉換,高層的決策和修辭閃爍多彩,民間對彼此的形象和認知也迷霧中偶見青天。此時再翻開這本小冊子,重溫並肩抗日時的舊時光景,眼前閃過七十年的波譎雲詭。
這批書中最老的一本是線裝的梁啟超《戊戌政變記》,1936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一百五十七頁。八十年的歲月將書頁化為棕褐色的薄脆,書脊、邊角不知經歷了多少磕磕碰碰,又破又碎。輕輕翻開,一股好聞的「舊」味兒。這本破破爛爛、只能捧着用指尖小心翻閱的《戊戌政變記》有趣就有趣在它的經歷。封面蓋了三個大概是藏書章,陽文「楊啟壯 K. C. Yeung」及在紐約的地址。略查資料,得知楊啟壯(1891-1958)是廣東新會人,梁啟超的同鄉,好像曾支持孫中山並加入過同盟會,1928年到1958年任紐約中華基督教長老會主任牧師。如此看來,楊牧師買《戊戌政變記》,良有以也。不過,他是在哪裏買的?上海,還是其他城市的某個書店?書又是怎樣隨他橫渡太平洋和美洲大陸,來到紐約的?書的內頁還有英文「CU東亞圖書館藏書」及「清倉」字樣。CU大概應指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楊牧師生前或過世後,書捐給了哥大。十幾年、幾十年過去,某天圖書館清倉賣書時,這本當時大概品相還不算太壞的書,吸引了一位年輕研究生的目光。陪伴她幾十年後,又成為我的案頭之珍。當然,還有另一種可能:哥大東亞圖書館不知從何途徑購入此書,若干年後清倉出售時,為楊牧師購入……若非書頁上當初或許無意印上或寫下的文字,它就將永遠保守自己身世的秘密,彷彿百年、千年之前傳下來的一件沒有印鑒的玉器、一首沒有序的詩。後人把玩之,吟詠之,回溯千百年前的情形,卻永遠無從得知。而有時,一行小序、一朵閒章,就能告訴我們它的作者,它古往今來無數擁有者之一,以及他們在歷史長河的某一刻那瞬間的得意或哀愁。
外文出版社翻譯的任繼愈《中國哲學簡史》本身無甚可談,但書中夾着的一張倫敦軻烈(Collet's)書店的收據卻令人神往。收據上的老式打字機字體告訴我,1960年4月,北達科他大學哲學系系主任Dale Riepe向軻烈郵購兩本書,一本就是任著,還有一本是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加上郵資一先令八便士,共計十七先令二便士,也就是不到一英鎊。Dale Riepe生於1918年,好像還在世。軻烈當年是有名的左派書店,有大批關於中國的書籍,董橋七十年代曾慕名前去一遊,買了幾部六十年代中華書局出的舊書,包括線裝《後漢書》,覺得價錢比香港舊書舖公道。軻烈書店九十年代歇業,《中國哲學簡史》則從哲學系教授的手中,繞了幾個彎後轉到了我的架上。
一個人是怎樣聚起一架書的?一個人的藏書又是如何散失的?鄭振鐸自稱「余聚書二十餘載,所得近萬種。搜訪所至,近自滬濱,遠逮巴黎、倫敦、愛丁堡。凡一書出,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無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節食不顧也。」錢穆三十年代在北平節衣縮食,購書約二十萬卷,還跟朋友開玩笑說,一旦學校解聘,自己還可以擺個書攤,不愁生活。這是刻意搜求。董橋在倫敦舊書店偶遇吳世昌的《紅樓夢探源》;汪曾祺戴着「右派」的帽子下放張家口勞動時,在小鎮新華書店一排排的毛選和講化肥農藥計劃生育的書之間發現《夢溪筆談》、《容齋隨筆》;我在華盛頓州小鎮舊書店角落找到商務印書館1933年「國難後第一版」(指一.二八事變及其後所受業務重創)《石頭記》,這都是可遇不可求。鄭振鐸的大批藏書在日軍進攻上海時化為灰燼。盧溝橋事變後錢穆倉促離京,藏書盡留原宅中,再無機會返回取書,遂流散各地。後來錢穆在香港時,友人買到一部《資治通鑒》,一看竟是錢穆之兄的書。此書是錢穆特地從蘇州家中帶去北平的,不知多少人經手後又現身香港,回到錢穆身邊。《通鑒》、《石頭記》,可惜都說不出自己輾轉流離、穿越時空的經歷。涓滴細流匯成大海,又化為雨水、雲朵,飄散到未知的地方,再次因緣聚合。
天上掉下的這十三箱書,單是如此賞玩、聯想,就足以消閒,何況真的一一展卷而讀呢?我有幸生逢其時,有看書買書存書扔書的自由,且沒有失書的苦惱,但另一種苦惱卻在於好書太多,讀不過來。雖然不必每本都讀,不必每本都從頭讀到尾,但辦公室和家裏書架上沉甸甸的上千卷,還有存在硬盤裏的電子書,已經遠遠超過了我此生文字處理的能力。這些書因我而聚,因我而散,我也不過是時間長河中的一個暫時的擁有者罷了。在這短暫的數十年浮生中,擠滿書架和硬盤的書帶給我的是快樂還是威壓,一時還難以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