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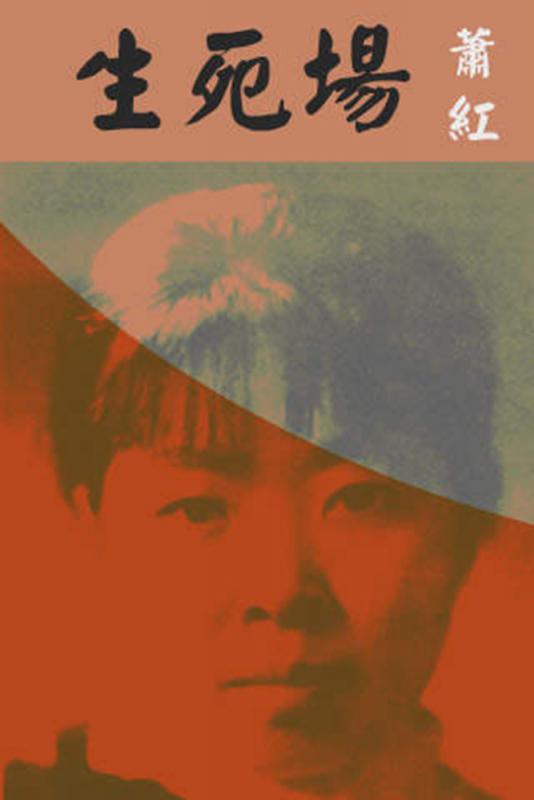
圖:蕭紅作品《生死場》 網上圖片
我家從前也有個小菜園,母親把四五分地打理得井井有條,一叢叢的韮菜,爬了老高的豆角,茄子葉瘦瘦弱弱的,但結出來的果子卻又大又亮,紫瑩瑩的,彷彿能照出人的臉膛來。
母親愛吃豆腐,在園子裏種了好多的蔥。一排排的小蔥整齊的立在春日的陽光裏,吮吸着露水,茁壯得彷彿像胖娃娃似的。顏色中有種綠叫葱綠,就是這種飽滿而結實的綠色,還有韮菜,汪曾祺曾說「秋末晚菘,春初新韮」,尤其是這在春雨中生長的韮菜,吸足了大地的春風雨露,機靈靈的就長出來,割一茬包了韮菜雞蛋餃子,不多幾天再去看,又綠油油的長出來了,頗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勢頭。
母親一般在農忙的收工之後去收拾菜園,東方微微露明,或是西方飛滿晚霞時,她總是提了半桶水,拿了水瓢,到菜園去拾掇。澆了水,順手在旁邊的老樹上折下老樹枝給豆角紮下爬藤,給黃瓜紮下幔子,還有番茄的小枝芽,被水沖得歪歪斜斜的,用舊衣裳的布條固定在枝蔓上。我那時下了學,總要幫忙去澆水,最開始提了小半桶水,後面個子愈長愈高,就開始用扁擔了,擔了兩個小鐵桶水,從家門口的壓水井挑過去。開始是左搖右晃,在小路邊灑了好多的水,都灌到了路邊的野薺菜了。
回想起來,那時天上風吹的滿地跑,又是春天草長鶯飛的日子,真想念母親的那片菜園啊。
思想從簡單到複雜是一條不歸路,蕭紅這筆下的故鄉也是永遠回不去的地方。
蕭紅筆下的人物,都帶着鮮明個人和時代特點。那小街上賣豆腐的豆腐西施,那龍王廟的教書先生,讓人可悲可嘆的有二伯,還有老廚子,小胡同裏的小團圓媳婦,還有磨坊裏的馮歪嘴子……這人間的一齣大幕,生老病死,酸甜苦辣都通過蕭紅兒時的眼睛一一折射出來。
鄉村那片土地的苦難,愚昧,開心,嘮叨,都在這些平常人家的口中蔓延出來。那小團圓媳婦的婆婆說:
「養雞可比養小孩更嬌貴,誰家的孩子還不就是扔在旁邊他自己長大的,蚊子咬咬,臭蟲咬咬,那怕什麼的,哪家的孩子的身上沒有個疤拉癤子的。沒有疤拉癤子的孩子都不好養活,都要短命的」。
「我對孩子真沒有嬌養過。養活孩子可不是養活雞鴨的呀,養活小雞,你不好好養它,它不下蛋,一個蛋,大的換三塊豆腐,小的換兩塊豆腐,是鬧着玩的嗎?可不是鬧着玩的。」
這小團圓媳婦的婆婆的話,讓人不忍心去痛斥她,這是在很遠的一片土地上的一代人生活記憶,不預約希望,看不到光明,也不苦大仇深的悲戚,這片土地上的人就是照着幾千年傳下的習慣生活着。但是字裏行間蕭紅透出的那份徹骨的悲涼氣氛,從兒童的眼睛傳達出來的,是參透人生五味的沉鬱。
蕭紅的文字平凡樸素,可這字字句句中又蘊藏着多少的心腸,那是她內心最隱秘的一片天地,沒有精巧的布局,但都是從內心深處噴發而出,熱烈,舒暢。
蕭紅自己曾說「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她的一生堅強而柔嫩,大氣又敏感,對她所有的作品而言,離開了那個時代,我們能領悟到的只是皮毛而已。她的情感和大悲喜通過文字造就了她的巔峰之作,也給我們留下了這首回響至今的絕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