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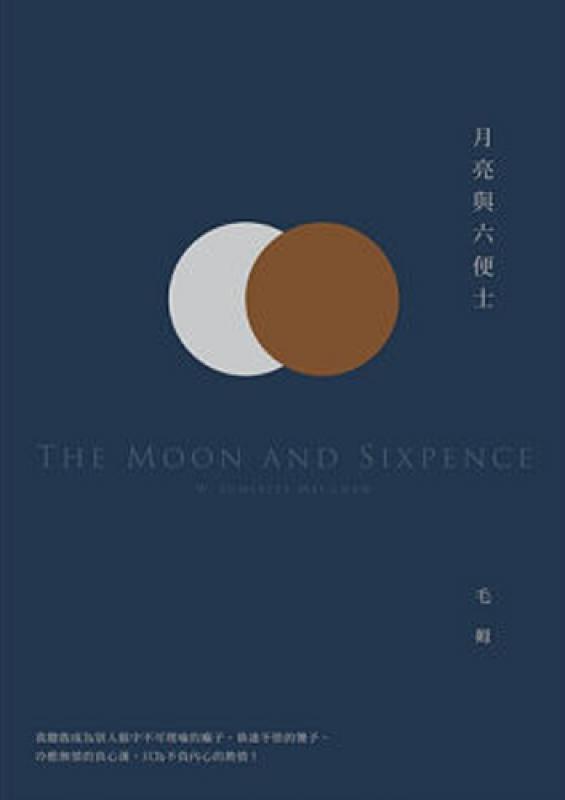
圖:《月亮與六便士》取材自畫家保羅.高更生平故事
民謠似乎在一夜之間變成了主流音樂,那些背着結他,嗓音低沉,不需要技巧的民謠歌手成了大眾情緒的代表。仔細想一下,流行起來的民謠,多半都是表達對過去的緬懷或理想照進現實時的失望,喜歡它們的人大部分都是三四十歲,經歷了年輕和生存之後不久,還不到了然的階段。說白了,就是曾經的少年開始衰老了。
理想這個詞,我一直不太理解,那似乎是年輕時代就清楚自己今後想要怎樣的生活。我不具備這樣的能力,20歲的時候,無法想清自己想要什麼。現在感到失落的,該是自己還是沒有找到自己吧。不知不覺間長大了,到了成家立業的年紀,結了婚,有了孩子,看起來也圓滿,但自己是什麼呢?自己喜歡什麼?誰還敢想這個問題,或者一直就沒想過,忘了還有這個問題的存在。
如果真的有理想,怎麼算達成?工作成功,有了社會地位,生活完滿,這些標準都太功利。能達成的基本都不是理想,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做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無論是否活得令人羨慕,這是對得起自己。
毛姆的小說《月亮與六便士》在1919年就思索了眼前的苟且、詩和遠方這個現在流行的話題。不為世人所理解又做着為人唾棄的事情的天才畫家史崔藍,過了讓自己滿意的一生,俗氣一點的說法就是活出自我,觀後由衷感嘆太難了。毛姆寫了一個理想化與苟且現實抗爭的「渣男」,他拋妻棄子,放浪形骸,甚至佔有朋友的妻子後又把她拋棄,他內心始終在衝撞,他採取了放任態度,完全拋棄了人間現實的各種標準。他是個天才,天才無法存活在股票經紀的體內,他不知道自己可以做到什麼,但知道自己必須要做些什麼,他要去尋找,要放低生活的需要,放低清規戒律,讓自己去感受和盡情的表現。
這不是個好人,也不需要必須是個好人,而是忠於自己的人。他的畫不是技術產物,先是感知的宣泄,最後發展到對世界的感悟。他知道自己在生命最後階段,在牆上完成了傑作,成就了自己的願望,人生完滿,但他要妻子在他死後燒掉它,「他創造出一個世界,他看到其美好。接着出於自負和輕蔑,他毀滅了它。」 (二之一)
虎哥 單身男青年,法律專業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