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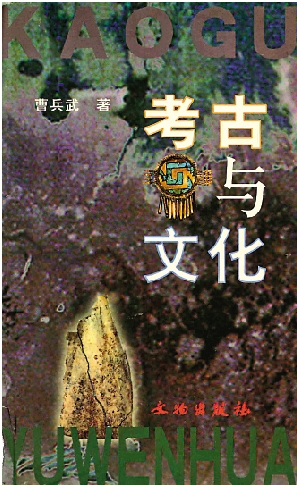
我自1994年開始在香港藝術館當上導賞員,此後不但對研究中國文化產生了興趣,亦開始閱讀一些博物館學的書籍。家中的書櫃盡收近20年所出版有關博物館學的中文書籍,而我每次出外旅遊時,博物館是必到之“景點”。1999年時,我與太太曾到澳洲的國立博物館參觀,發現其藏品甚為國際化。負責人的野心不少,他們想辦出一間國際級的博物館,當時正在舉辦塞尚的畫展,令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回港後,我找來曹兵武的《考古與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一讀,書中正有一文,是介紹美國博物館的國際化特點,文中所提的觀點,值得我們反思。
美國博物館在陳列設計和服務方式等方面具有自己獨特的形式,並具有國際性。除了一些專門的博物館外,一般博物館則完全是一個國際文化與藝術的殿堂,在同一空間內,展示?世界各主要民族文化的歷史成就。其中如波士頓藝術館的埃及文物,其數量之多、價值之高,據說除了開羅的埃及國立歷史博物館之外,無有其匹。
有些文物,則默默記錄?美國近現代歷史的輝煌:一支支的考古隊伍,隨?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軍事實力的到處擴張和滲透,被派向世界的各個角落,他們帶回了無計其敵的“收穫”,其中包括這些文物。但是,國際化的博物館,也是反映不同文化價值衝突的窗口。在歷史洪流中,一些民族及文化的興旺發達,往往同時意味?另一些民族與文化的受辱蒙羞。埃及、兩河流域、印度、中國等地區,幾乎無一個逃出列強考古學家的染指。而這些文明中的驚人的輸出,正是構成西方現在各主要博物館展品的核心。
上世紀最初二十幾年間,在中國考古學的早期歷史上,也有一段這樣的恥辱歷史,那就是大量的絲路之文物被一再掠奪。例如美國人瓦納領導的三人小組,曾在敦煌偷走了壁畫及佛像,行徑極為無恥。去年八月,我參與了由教育局官員李志雄、李淑賢帶領的敦煌文化考察團,參觀了數十個洞窟,大開眼界。其中亦有進入瓦納偷走壁畫的洞窟,想到他當年無法無天的行為,實為我中華民族國力不彰,受外侮所欺之結果。
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