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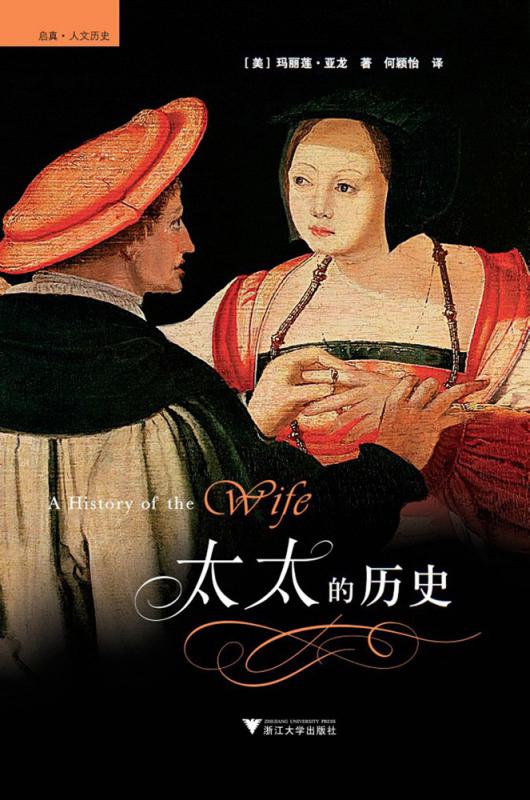
圖:亞龍(Marilyn Yalom)著、何穎怡譯《太太的歷史》(浙江大學出版社,二○一六年十月)
《紐約時報》書評作者Laura Shapiro在介紹《太太的歷史》(A History of the Wife)這本書時,曾提出一個頗為直白卻引人深思的問題:為什麼會出現專門介紹「太太」歷史的書,而關於「丈夫的歷史」的書寫卻遲遲不見蹤影?
李 夢
問題問得非常妙,妙到我們常常忽視了它的存在。的確,本書作者亞龍(Marilyn Yalom)與一眾學者或記者曾各自寫下檢視「太太」或者「妻子」這一名詞流變經過的著作,卻少有文章及專著從同樣的角度探討「丈夫」的概念。千百年來,「男性主導+女性從屬」的婚姻關係幾成定式,以至於太太的角色從來都是被動的、不聲張的。女性在婚姻中被有意或無意地擺在等待的狀態裏——她們時常是沉默的,等待被解釋、被發現乃至被拯救。
在一些人看來,「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這句話再正確不過,而男人與女人也將是兩類注定無法彼此理解的物種。我雖說並非這一論點的忠實信徒,卻不得不承認男性及女性在思考及處理問題上的迥然分別。本書作者是女性,也是一位溫和的學者,在史丹福大學從事女性及兩性研究多年。學者身份幫助她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做到條理清晰且引證充分,不偏不倚,盡量客觀,而女性身份則使得她在回望女性地位及婚姻關係變遷歷史的時候,更容易準確拿捏當事人細膩敏感的心理,也易於引起讀者的共鳴與同理心。
《太太的歷史》英文原版於二○○一年初次面世,而這書的中譯本直到二○一六年才由浙江大學出版社以「啟真館」叢書的名義發行。十五年後,中文譯本姍姍來遲,並未激起坊間太多議論。而在這十五年間,全球的社會、經濟及文化形勢都發生了顯著變化,書中觀點在當年或許新鮮,可放在當下語境中看,已無法回答兩性關係以及婚姻中出現的許多新問題了。
這部由學者撰寫的歷史著作行文克制,不願摻雜過多個人觀點與情緒,力求客觀。本書依照編年順序寫成,從希臘與羅馬時代妻子在婚姻中的角色及功能,一直講到二十世紀下半葉現代女權運動高漲之時及之後,妻子在婚姻中以及在職場上面對的顯而易見的轉變。全書分為十個章節,主要選取美國以及歐洲兩地婚姻生活案例為樣本,上至皇帝及貴族,下至小民百姓,案例中人的身份與背景盡可能地全面豐富。
婚姻無愛「太太」更像工種
作者在敘述中並未涉及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域及文化中的案例,一來因為她的學識背景及研究範疇所限,二來因為這些地方現代化進程的開啟遲於歐美,相關歷史資料未必豐富。將來,如果能有熟悉中國歷史的學者有心寫一本《中國太太的歷史》,從秦漢時期爭風吃醋的皇帝妃嬪寫到唐代妻子的獨特裝扮,再寫到二十世紀初上海灘風華絕代的旗袍女子,應是十分豐富且精彩的文本。
話說回來,亞龍儘管在書中僅僅提及美國、英國、法國與德國的案例,詳實或簡要地提到不同時期及不同地域的太太的故事,內容卻已足夠飽滿,且具有相當的普適性。我們不難發現,那些曾困擾十九世紀美國已婚婦女的問題,也曾困擾過歐洲中世紀的婦女。作者旁徵博引,從現實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報刊文章、文學與戲劇創作、電影乃至街頭巷尾流傳的童謠等不同種類及性質的文本着手,從大量的細節與看似微小的證據中,提煉出本書中最為重要的觀點:婚姻並非從來都是因愛結合的關係。在十六世紀之前,男人與女人走入婚姻殿堂,大多出於財務及雙方家境的考慮,而非由於兩性間單純的愛慕;在十六世紀之後,資本社會逐漸發展,中產階級出現,因愛締結、以自由及自願為基礎的婚約才越發普遍,兩情相悅以致永結同好才成為婚姻關係中的常態。
在中世紀乃至更早時候的婚姻中,攜手步入婚姻的男女大多情況下只是聽命於父母之言而結合,並非出於真心相愛,故而,丈夫與妻子的關係至多只是相敬如賓,甚至丈夫還被允許打罵妻子,而妻子則必須要盡心盡意服侍丈夫與孩子才可免於責罰。在那樣的社會氛圍中,「太太」更像是一個工種,而非某種身份的象徵。直到十八世紀啟蒙時期之後,丈夫在婚姻及家庭生活中才開始學着尊敬妻子,夫妻關係才逐漸趨向平等與互相尊重的樣態,夫妻之間長久以來建立的合作模式——「男性權威+女性服從」以及「男性保護+女性忍耐」——也漸漸被改寫。由是說來,婚戀關係中妻子地位與身份的轉變,也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女性在社會中地位與身份的變遷。
「太太」這個概念可以被放入兩重語境中講述:她們既是婚姻關係締結的一方,也是社會運轉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也就是說,作者在本書中藉由對於「太太」這個社會學名詞的梳理與探討,試圖解釋婚姻的多種樣態並藉由婚姻作為一個參照,來檢視社會發展進程中現代化(包括女權主義、平權運動等)的潮流及導向。
女性平權男人配合改變
《太太的歷史》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對於女性主動爭取權利的描寫。在第六章「維多利亞時期的美國邊疆妻子」以及第七章「女性議題與新女性」中,作者不厭其煩地引用十八、十九世紀美國女性的日記和信件等,從這些真實度高且私密性強的第一手資料中,呈現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現代社會中的女性,不論單身抑或已婚配的,都渴望能夠依照自我意願做事情。她們希望依照自己的意願挑選工作,進入或放棄婚姻,因而最終能成為自己命運的掌控者,可以扮演像《玩偶之家》中女主角娜拉那樣因不滿婚姻而摔門離去的角色。
儘管理想美好,現實卻並不盡如人意。但那一時期的女性不再躲避、自責或妄自菲薄,這種姿態及行動上的轉變,無疑為後世女性爭取自由平等提供了榜樣。作者引述女權先鋒Abba Goold Woolson的話,稱「我存在,不是因為我是個妻子、母親、老師,而是因為我是個女人」。這句話在今天聽來依舊震撼人心,更何況是在它初次面世的一八七四年,而如果沒有維多利亞時期女性的抗爭,十九世紀後半葉乃至今天的女性,應沒有勇氣說出這樣果決的話來。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回應了《紐約時報》書評人的問題:為什麼我們寫書談論「太太的歷史」而不是「丈夫的歷史」?因為附着在「太太」這一身份上的責任太多了。廚師、保姆、清潔工人,如是種種。而且,數量眾多的書籍和電視節目不斷告訴我們如何成為一名合格稱職的太太,卻少有人議論「如何成為一名好丈夫」。似乎,丈夫只要每晚歸家、工資上繳,就足夠了。他們扮演「丈夫」角色時,不需要學習,而女性作為妻子,卻時時被提醒需要不斷學習以提升技能、獲得認可。你看,評判的標準從來不在女性自己手上。
書中用大量篇幅提及的女性主動爭取並抗爭的經驗固然可喜,但推動婚姻關係轉變乃至整個社會對於兩性關係認知的改變,卻不能單靠女性自己用力,男性的互動同樣不可或缺。如果時代發展到今天,男性對於「太太」的認知仍停留在馬丁.路德的勸誡中,認為女人除了「服侍男人以及當他們的幫手」之外別無其他能力的話,那麼兩性關係與女性地位將永遠停滯不前,更不用期待所謂新女性與新型婚姻關係的出現了。誠如英國書評人Frances Wilson在《衛報》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如果丈夫的角色不更改,妻子的地位很難改變。」只是,本書作者較少提及歷史演進過程中男性角色的配合與互動,實在是有些遺憾。
作者在前言中說,她與丈夫結婚四十六年,擁有平凡卻美滿的婚姻,她也「逐漸明白了妻子一詞背後隱含的豐富意義」。或許因為作者的婚姻與家庭關係都堪稱幸福,所以她儘管透過不同文化背景的案例談論婚姻中的曲折與不幸,卻對人類千百年間建立並維繫的婚姻制度抱持樂觀且積極的態度。在她看來,只要婚姻中的男女不斷探索相處之道,婚姻這一古老的概念必將不斷發展演進下去。可問題是:二十一世紀邁入第二個十年,我們是否還需要婚姻呢?
與波伏娃的《第二性》相比,亞龍的文字顯然更為溫和。她一直不曾放棄「女性渴望進入婚姻」的美好想法,可是如今的女性已不再像她們的媽媽與祖母那樣十分期待婚姻與俗世意義上完美的家庭關係了。她們可以選擇單身,可以與伴侶同居,可以與同居伴侶生下小孩並一同撫養,卻可以遲遲不邁入婚姻,不給自己冠以「某某太太」的名號。當個體追求自由與自主的權利不斷張揚,婚姻制度已然面臨根本性的改變乃至動搖時,我們談論「太太歷史」的意義與價值在哪裏?若《太太的歷史》將來出版增訂本,我希望見到作者對於這一問題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