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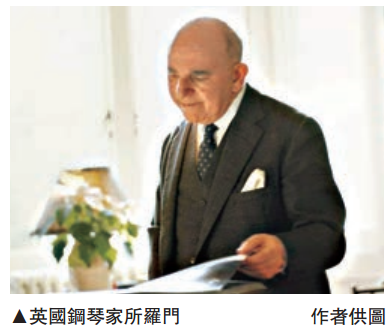
即便是像海明威那樣嚮往強悍與堅韌的人,也曾說過這樣的話:「除非你是鬥牛士,否則沒有誰的生活只進不退」。若是英國鋼琴家所羅門(Solomon Cutner,一九○二至一九八八)聽見這話,應格外受用。八歲已在倫敦女王大廳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的音樂神童,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達至事業高峰後,卻因一場突如其來的中風而被迫在輪椅上度過三十年餘生,因此,不論名氣抑或留給後世的經典唱片,都遠遠少於同齡的偉大鋼琴家如阿勞與霍洛維茨等。不過,即便是這樣寥寥十數張唱片,足以令他置身二十世紀偉大鋼琴家之列,成為德奧與俄國學派之外,為數不多的另類天才。
若我們回顧二十世紀世界鋼琴家名錄,不難發現其中佔據絕大部分的,是來自德奧與俄國兩個學派的藝術家。大致說來,德奧鋼琴家主要演奏貝多芬、舒伯特和布拉姆斯等德奧曲目,強調旋律中的理性與邏輯,注重音樂的思考性;俄羅斯學派眾人,傾心於鑽研柴可夫斯基和普羅高菲夫等人作品,關注旋律的抒情性以及演奏者的情感表達。這兩種學派加上法國學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呈現「三分天下」的態勢,以至於像所羅門那樣來自英國的鋼琴家,在如此強大且綿延的傳統面前,總或多或少顯得格格不入。的確,英國在過去一百多年間的偉大鋼琴家,用一雙手差不多已可數盡,甚至還要將傅聰和內田光子等後來定居倫敦的亞裔音樂家算進來。
在這為數甚少的音樂天才中,所羅門可說是相當搶眼的一位。儘管他早年大部分巡演活動都在歐洲尤其是自己的故鄉英國舉行,但為數不多的幾次美國之旅,便足夠讓當地的藝評人驚訝不已。《紐約時報》知名樂評人勛伯格在一九五五年聽過所羅門的紐約獨奏會之後,稱他為「最有教養的鋼琴家」;而新版格羅夫音樂辭典也在描述他的演奏風格時,用上「喚醒回憶的詩人」這樣的字眼。
「詩意」確是所羅門演奏風格中最值得強調的關鍵詞之一。古典音樂可謂英國藝文景觀的短板(與其璀璨的文學相比,古典音樂作曲家與演奏家着實少得可憐),而所羅門的成名,或也部分歸因於他的老師瑪希坦.維恩,這位德裔英國鋼琴家曾是克拉拉.舒曼的學生,對於德奧作品不乏研究。因此,所羅門在少年時代雖說曾接觸不少俄國曲目,但真正令他成名歐洲乃至世界樂壇的,還是他對於貝多芬和布拉姆斯等德奧作品的精妙演繹。有些音樂家如智利鋼琴家阿勞在詮釋貝多芬鋼琴作品時,傾向於表現出旋律中激越、衝動、極富張力的狀態,而這樣戲劇化的表達方式並非所羅門的習慣。
我曾在某段陳年影像中見過所羅門演奏舒伯特鋼琴奏鳴曲,舉止神情全然是英國紳士做派,一點誇張和炫技也不講,只是隨旋律與節奏輕微擺動身體,穩重之中偶見輕靈與生趣,與講求優雅得體的英倫氣質頗為契合。而這般氣質,在活躍在當今古典樂壇的英國鋼琴家如李維斯(Paul Lewis)等人身上,似也能見出些許蹤影,雖說李維斯與所羅門相比,仍略顯沉穩有餘而輕巧優雅不足。
人們不免唏噓,如果所羅門的最後三十年也像阿勞和霍洛維茨一般老當益壯,或許能為後世樂迷留下更多珍寶。但世事不會盡如人意,就像我們無法奢求貝多芬如果未患耳疾,會否寫出比第九交響曲更輝煌偉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