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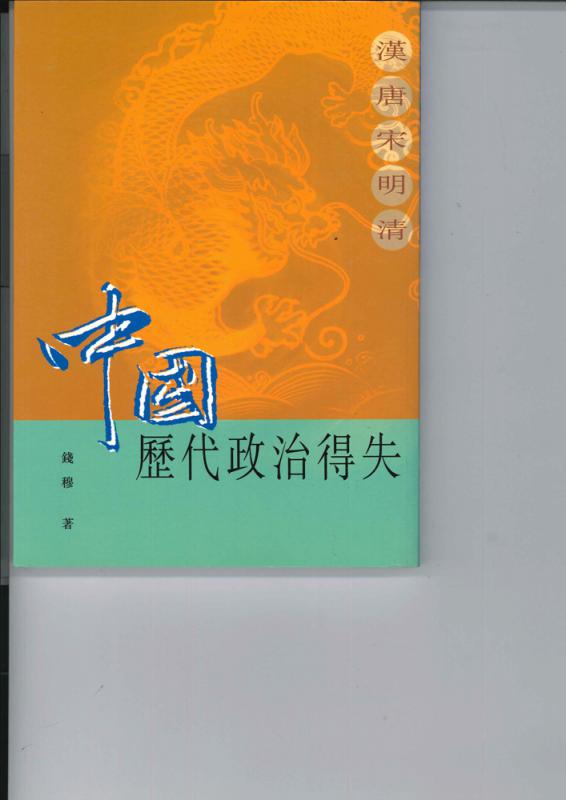
香港自50年代以來都是一個學習中國歷史的理想地區。我們在書局、在圖書館,可以找到不同立場的歷史著作;在各大學的歷史系中,我們有大批不同觀點的學者;在媒體中,更常有不同的人士談歷史,觀點雖然偶有標奇立異,但亦顯出了香港「史學」百花齊放的特色。
當然,香港史學界中最足以自豪的事,肯定是錢穆先生在上世紀50至60年代在香港的教學。我輩晚出,無緣一睹錢先生的風采,只能從他的傳世大作中,一窺其學術素養,習得一點皮毛而已。錢穆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香港:三聯書店,2004年) ,我翻閱不下三次,每次一讀,皆有所得着。能寫出這本超越時代的制度史書,除錢先生之外,當世應無他人。在〈總論〉一章,錢先生先探討了中國傳統政治上存在着不少問題,令中國在近代化過程中難以順利地轉型,然後他又提出未來中國政治和政制要成功地現化化,必須建基在傳統的「土壤」之上。
中國之將來,如何把社會政治上種種制度來簡化,使人才能自由發展,這是最重要的。但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是推倒,而在建立。例如建立民主制度,有人以為只要什麼事都待集體商量過,加上不停開會,便可稱為民主(正正指出了今天香港立法會的情況)。我們天天說中國的法治不足夠、民主不完善,其實不夠的應是人才。國家現在將如何酌採西方的新潮流,如何拿自己以前的舊經驗,來替自己打開一出路,來創新法,運用人才,這是當代執政者的責任。西方各國各自在創制,在立法,他們覺悟到有了毛病,還可改。我們如只是一意模仿抄襲,就不會有任何覺悟。西方各國自有其歷史,我們又如何能將自己橫插進別人家的歷史傳統呢?
錢先生對國家的發展觀,正是今天國家堅持的發展現代化方向,有論者稱這種方向為「中國模式」,成效顯著。反觀香港一些政客、學者,心中只有西方,無論談到任何改革,皆主「模仿抄襲」,盡見「不讀史」之弊。
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