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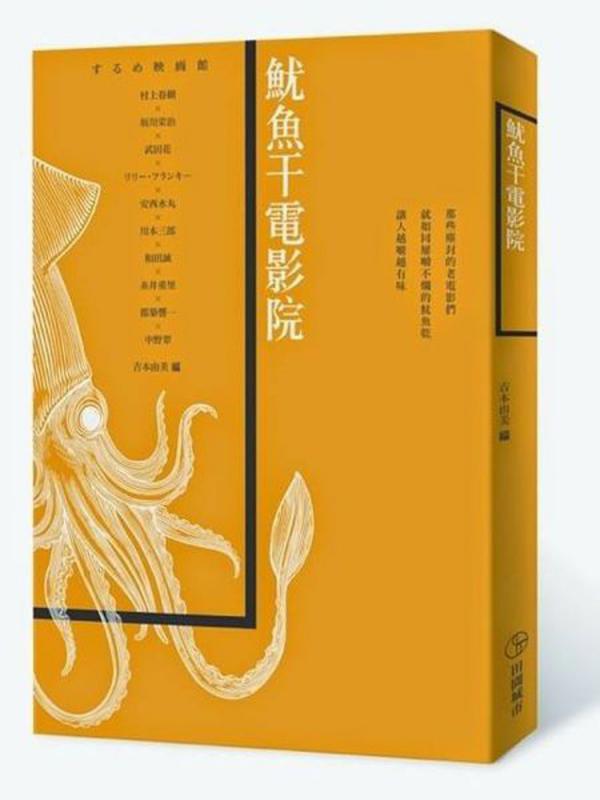
在我年歲還輕時,常聽老阿婆提起關於人在暮年之時的悲秋傷懷,那時阿公已經過世,兒女們也都去了很遠的他鄉。阿婆就搬到了鄉下一個小村落,在小村的東北角,守着佛台落落寡合的自己生活着。那時我資歷還輕,沒有經過生活大起大落,也還沒有走出去看過世界的不同角落,甚而無法了解老阿婆晚年內心的悲苦。
現在二十多年過去了,當我走過生活的坑坑窪窪,無意間讀到沈祖濂的《悼亡女文》,字字句句出自心底的血淚,回頭回憶起阿婆當年的心境,不由內心湧起一股柔情,那是對人間至情的一種體諒。
面對失去幼小女兒,沈祖濂寫到:「汝見冥世判官,則揖雙手拜曰:吾年幼,潔而無沾。生於寒素,足於薄粥。生時未靡費粒米隻粟,亦未敢稍忽衣屢,而今余成此文,汝尚未識讀之。余所能為者,惟慟哭狂號汝名矣。」
每句訴說都帶着血淚
還未長成的幼兒離世,為父在無盡的傷悲之中只能苦苦以文指引幼兒如何拜見冥世的判官,期望能由此減輕這幼兒獨自一人面對未知死亡的困難。父親明知自己的幼兒無法接收到這指引,可是還是要一一仔細的指點,寄託於這種方式能給幼兒做最好扶持。
文中沒有訴說自己怎樣斷腸,怎樣無盡的淚水哭嚎和悲傷,怎樣抱怨世時的不公奪去自己幼兒的生命,可是我們細細看這一句一句的訴說,都是帶着血淚:告訴幼兒見到冥世的判官,說我還年幼,還未長成大人,一身潔淨而來,又一身乾淨的死去,從小生長於貧寒之家,在活着的短暫時間裏,也未曾浪費過粒米隻粟,亦從不敢在衣裝上有稍微的奢靡。
父親希望通過這樣的表述,能減輕幼兒在冥世的苦難,這種無望的希望帶來的傷痛更是無法用語言來形容,各種悲苦只有在心底。
唯一能做只有叫孩兒名字
最後在所有指點完之後,這位父親才意識到,他的幼兒永遠無法看到父親的指點,因為「而今余成此文,汝尚未識讀之」,逝去的幼兒太小,還不會識字,那麼所有的指點也都成了空想,想減輕幼兒在冥世的苦難也成了奢望,身為父親,唯一能做只有苦苦痛哭叫着孩兒的名字。這最後簡簡單單的字句,彷彿古今一夢盡荒唐,讓人無盡的淚人漣漣。
古人說一生一轉眼,一夢一千年,面對悲歡離合與人世的變遷,哪怕經歷過這麼久遠的歲月,我們對人間的至情仍是一樣的滄桑心境。這也是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在被傳頌了千年之後,仍在我們心中引起震顫和漣漪的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