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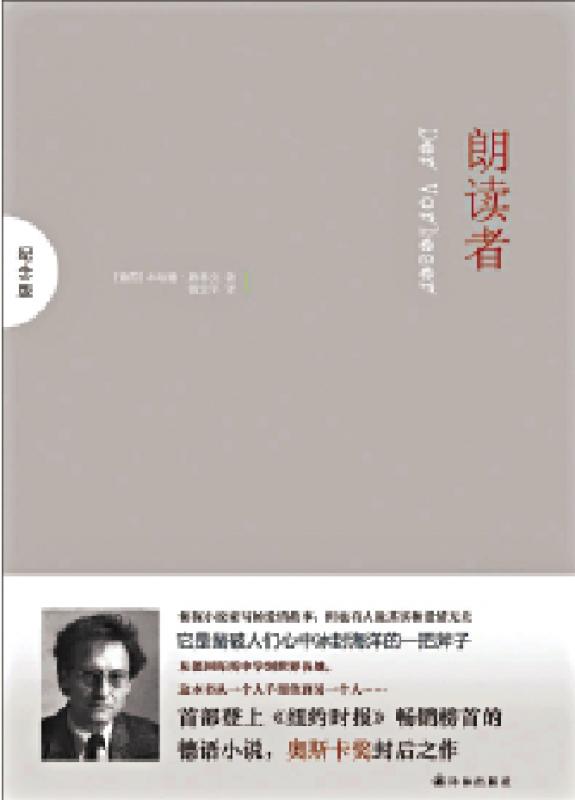
圖:《朗讀者》內地譯本,譯林出版社
「雪崩中,沒有一片雪花覺得自己有責任。」
斯坦尼斯洛的名句,道出了歷史的弔詭,也道出了每一個平庸的惡者內心的狡猾與麻木……
他們如此篤定於自己的行為,做一片盡忠職守的「雪花」。
勇敢者,可傾覆自己,面對荒涼過後的泥濘;懦弱者,抱殘守缺,了此一生。
重讀《朗讀者》。
這本書的意義,總覺得,在於重溫。不同的年齡閱讀,會有相異的認知與結論。這意義或許和堅執相關。但是,換一個角度來說,它亦會提示,用一己的價值評判體系去估價他人的行為,是愚不可及的事。
初讀時,很容易將之總結為兩個失敗者的故事。漢娜和米夏,在各自的人生中逸出軌道,進而改變對方。歷史的顛覆中,難以全身。一個罪惡深重,一個肩負陰霾。這場角力,以少年的情慾開始。「如果貪婪的目光像肉慾的滿足一樣惡劣,如果主動想像和幻想行為一樣不堪的話,那麼,為什麼不選擇肉慾的滿足和幻想的行為呢?我一天比一天地清楚,我無法擺脫這種邪念。這樣,我決定把邪念付諸行動。」但最後敗下陣來的,也是他。他投入了愛,不僅因迷戀這個女人豐熟的肉體,在一次又一次的衝突中延宕與遷就,同時間,他從未意識到,自己的一生輸給了一個秘密。漢娜的失蹤與藏匿,突如其來。他們儀式一樣的幽會,已千篇一律。洗澡、朗讀、做愛。他為這個女人朗讀,以他們的母語。《奧德賽》、《戰爭與和平》、《一個窩囊廢的生涯》。比起性事,她似乎對此甘之若飴。
私人罪感與公共罪感
在她不告而別之後,重逢已是在法庭上。米夏以法律系實習生的身份,列席納粹集中營罪行的審判。而被告之一,正是漢娜。漢娜在二戰時期做過納粹集中營的看守,因對三百多名猶太囚犯的死亡負有責任而受審。米夏心中的煎熬隨審判的進行日劇加深,而漢娜往日的秘密也初現端倪——她是個文盲。她一直保守着不可言說的秘密。而她的一生,也為這個秘密而左右。「她害怕暴露出來。這也是她拒絕被培養成電車司機的原因,因為做售票員可以掩蓋她這個缺陷,而一旦成為司機,弱點就非露餡不可。這也是她要離開西門子公司,而去當一名看守的原因。這也是她自己承認寫了報告,而拒絕邀請專家來鑒定筆跡的原因。」漢娜攬下了所有的罪名,最終被判終身監禁。米夏為自己明知漢娜的秘密,但卻沒有勇氣替她澄清罪責而負疚,私人罪感與公共罪感──為納粹期間「德國罪過」所負有的罪感──之間形成了衝突,也為「二代記憶」提出了它所特有的記憶倫理難題。
這構成了在八年以後,米夏再次成為朗讀者的起點。其間,他經歷了失敗的婚姻,乃至受挫的性愛。他尋找過的每個女人,都有漢娜的輪廓。他重讀《奧德賽》,發覺這個故事,說的不是回歸,而是重新的出發。於是,他又開始朗讀,並錄音,將它們寄給了服刑的漢娜。施林茲勒、契訶夫的短篇小說,海涅與默里克的詩歌。第四年時,他收到了漢娜的回信。「小傢伙,上個故事很特別。謝謝。」漢娜依照他寄來的磁帶,與書籍的閱讀,學會了寫字。
以「無知」開始 以「文明」結束
是的,看到了這裏,我怦然心動。類似於某種邏輯的打通。不是文學的邏輯,而是漢娜人生的邏輯。她終於可以真正通順地梳理自己,而非一味無原則地羞愧。她一生的罪感,起初來自於掩飾。掩飾的是自己與文明之間的鴻溝。不惜卑微地退縮、企圖泯然眾人。但當她學會了讀寫,卻清晰地發現,自己更為深切的罪。在獄中,她找來閱讀的是猶太人幸存者的文學作品──普里莫.萊維、埃利.維賽爾、讓.艾默里(Jean Améry)等人寫集中營的書,還有赫斯的罪行錄與阿倫特關於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被處絞刑的報告。
書中並未以任何敘述視角透露,這些作品給予漢娜的影響。但她在自盡之前,十分妥貼地安排了將自己一生的積蓄,留給了指向她罪行的那場大火中唯一的幸存者,一位猶太裔的女作家。
這其間有清晰的隱喻意義。她作為戰犯,向德國「二代記憶」的記錄者所表示的懺悔與救贖。而這一切,以「無知」開始,以「文明」結束。小說未寫其覺醒,但卻在法庭上借漢娜之口,質問了法官,「此時此境,你會怎麼辦?」
「文盲」是一個簡單粗暴的解釋罪行的理由。而深諳文明內核的社會精英,曾如漢娜一樣地做出自我的選擇。這是戰後的德國,在不斷強化對道德機制的開啟,重新反思過去的綿長過程中,積極致力面對的問題。「雪崩中,沒有一片雪花覺得自己有責任。」斯坦尼斯洛的名句,道出了歷史的弔詭,也道出了每一個平庸的惡者內心的狡猾與麻木。漢娜或是幸運的,因其「文盲」的身份、支離破碎的知識體系。「識字」的過程,造就其重新認識世界和自我的過程。在冒昧中撥雲見日。而精英者,代表着這世界上的擁有朗讀權力、卻甘於「默讀」的人。他們和文明之間,存在着自欺欺人的斷裂。他們如此篤定於自己的行為,做一片盡忠職守的「雪花」。勇敢者,可傾覆自己,面對荒涼過後的泥濘;懦弱者,抱殘守缺,了此一生。
在這個過程中,文明乃至藝術,扮演了什麼角色。德國戲劇家彼得.史耐德回憶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奧斯威辛審判時他參加學生運動的情形。他所關注的是,如何處理在家庭結構中面對父輩的感情,與將之放在歷史節點評判時所帶來的道德困惑。他的父親是一位作曲家和樂隊指揮,他說道:「就在我們反叛的時候,我們也盡力保護自己的家庭。我們從來沒有問過父親這個顯然該問的問題:當猶太人音樂演奏者一個個被清除出樂隊的時候,你做了些什麼?」可嘆的是,這個問題,恰與一部電影構成了微妙的互文。
這部電影叫做《鋼琴家》(The Pianist),取材自波蘭猶太裔作曲家和鋼琴家華迪史洛.史匹曼(Władysław Szpilman)的回憶錄。其恰從受害者的角度,對這個問題給予了回應。史匹曼在迫害中流離,偶遇德國軍官威爾姆.歐森菲德,被認出是猶太人。問及職業時史匹曼說自己是一個鋼琴家,於是被要求演奏一曲。史匹曼演奏了蕭邦的第一號敘事曲,琴技折服了歐森菲德。他因此決定協助史匹曼躲藏,並定時提供生活所需。不言而喻,這對於史匹曼最終逃出生天提供了重要的幫助。軍官的設定,亦符合《夜間守門人》式的刻板印象。表面上看,由於藝術的共情性,造就歐森菲德施以「小善」,從而保留了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但究其底裏,史匹曼得以幸存,並非因為他是一個猶太人,甚至是「人」,而是因為他是傑出的藝術載體、他精湛的技藝。得以全身,恰在於其本人被充分地「物化」。藝術家超越國族立場的個人經歷,並不鮮見。在巴黎尋求政治避難的前蘇聯芭蕾舞者雷里耶夫,也是一例。我曾經在《北鳶》中寫到京劇名伶言秋凰,為票友和田中佐所賞識,納為知音禁臠。但成敗一蕭何,因為對京劇的痴迷,其最終為前者所刺殺。完成了民族大義的言老闆,說到底,恰是實現了從藝術的替代物,最終覺醒為「人」的過程。
通過朗讀完成自我救贖
某種意義上說,「朗讀者」米夏,也是一個載體。他承載了「過去」的文明的總和,也代表着過去向現在的發言。面對「無知」的打破,「朗讀」的意義,並非是摧枯拉朽式的,而是綿長、溫和、潤物無聲的。它的漫長,提供了一個個可供思考、反芻與咀嚼的空間,並與少年的成長,同奏共跫。事實上,少年成長或許是認識歷史最為直接的鏡像。或許殘酷寫實,如君特.格拉斯的《但澤三部曲》,其中以《鐵皮鼓》和齊格菲.藍茨(Siegfried Lenz)的《德語課》(Deutschstunde)(一九六八年);或許如哈哈鏡,是喜劇外衣下的陰翳,笑中有淚,如貝尼尼的《美麗人生》。但總有着某種清晰而切膚的銘刻。何況,《朗讀者》的因由,是一名成熟女性對少年情感與肉體的餵養,在這面目嚴正的民族文學譜系中,莫名地有了象喻的禁色之美。
在一次纏綿的旅途之後,米夏寫了一首詩,模仿自他彼時正熱烈閱讀的詩人里爾克和貝恩。這首詩如此貼切地表達了他對漢娜的感情,或許亦可視為一首唱給歷史的輓歌:
與君同心,兩心相互來佔有/與君同衾,兩情相互來佔有/與君同死,人生相互來佔有/與君分袂,各自東西不回首。
(文中小題為編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