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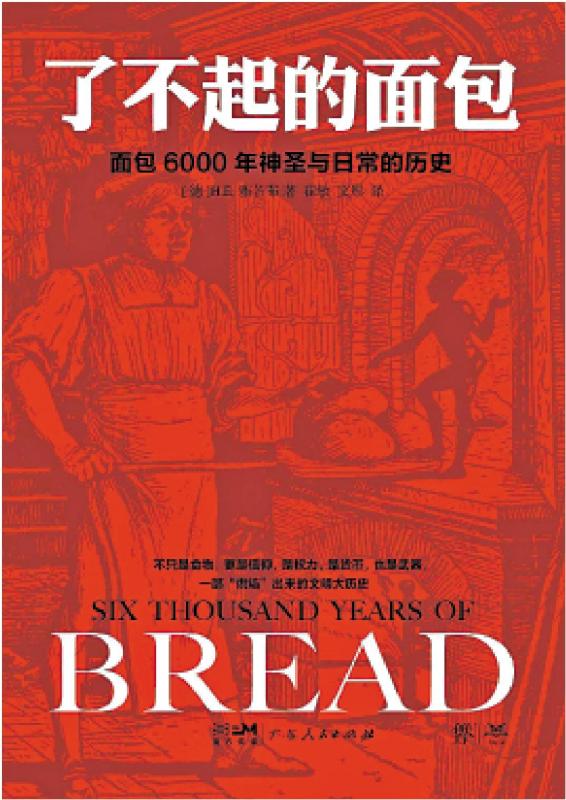
圖:雅各布著《了不起的麵包》。
有誰能想到,在英國,一條價格不等的麵包,不止是填飽肚子那麼簡單,它背後還牽扯到財富和階級等因素,最基本的食物如何成了分化和衝突的根源?
不久前,一位劍橋大學教授發現,他家附近的手工麵包店最便宜的黑麵包要五英鎊,而超市裏最便宜的切片白麵包只要四十五便士。他不禁在報刊上撰文抱怨,稱麵包只需要四種成分──麵粉、水、酵母和鹽,─樣的東西怎麼會在價格上相差如此之大?原因就在於手工麵包店是打着「精英主義」的旗號收取昂貴的費用。他的結論立即引來市場人士的反駁,指出超市的切片麵包之所以賣得便宜,得益於超加工等現代技術,大工廠的機械化生產提高了勞動效率,比起手工製作成本更低。
雖然兩個人表面上爭論的是麵包價格,但實際上卻是英國長期以來「麵包戰爭」中的一部分。如同英國作家彭.沃格勒在《嘲笑:英國食物和階級的歷史》一書中所說,麵包是我們飲食的基礎,但就像很多事情一樣,它與階級息息相關。有關社會地位和麵包顏色的觀念可以追溯到羅馬時代,當時領主的麵包是雪白的,而其家中下人的麵包都是黑色的,因為生產白麵粉需要花更多時間和金錢,意味着麵包的顏色決定了人們的社會地位。
沃格勒所說的白麵包,在中世紀確實是稀罕之物,那時小麥被壓碎在石頭之間製成麵粉,再將麩皮、胚芽和胚乳混合在一起,然後過篩以使其更白,專供有錢人享用。因而七八個世紀以來,白麵包常與富人聯繫在一起,黑麵包與窮人聯繫在一起。作家斯科特.尼爾森在《小麥戰爭:穀物如何重塑世界霸權》一書中提到,由於物資匱乏,英國的窮人有時即便是黑麵包也吃不到,英格蘭多次發生窮人爭奪口糧而爆發的「麵包騷亂」。就算到了維多利亞早期,情況也沒有出現根本性好轉,著名醫學雜誌《柳葉刀》就記錄了維多利亞時代消費者對於麵包的需求:「越白越好,越便宜越好」,於是麵包商們開始公然造假。如果說中世紀窮人的黑麵包難以下嚥,那麼維多利亞時期的麵包就是有損健康。以一八三八年為例,一磅重的麵包相當於工人一天的工資,商人為了謀取暴利,常往麵包粉裏摻雜廉價過期麵粉、土豆粉、豌豆粉,以及其他可疑雜質,比如加入白堊粉,為的是麵包能吸收更多的水分以虛增重量,而加入明礬,則是為了使麵包外觀看起來更像高級的白麵包。
直至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出現了鋼製滾筒,可以將棕色麩皮和油性胚芽剝落,瞬間製成白麵粉,工人們才真正意義上吃到白麵包。用沃格勒的話說,幾個世紀以來,人們一直被告知白麵包對基層這樣的人來說太好了,因此他們想吃上白麵包也就不足為奇了。但即便如此,隨着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普通階層仍擺脫不了吃黑麵包的命運。作為島國的英國由於嚴重依賴糧食進口,一九一六年推出的戰爭麵包雜糧含量高達百分之七十六,在海上貿易路線被德國潛艇切斷後,戰爭麵包雜糧含量突破百分之八十。然而,到了一九一八年初,戰爭麵包雜糧含量已經高達百分之九十二,而且還加入了大豆、馬鈴薯這些非穀物成分,烤出來的麵包也變得更黑。
值得一提的是,作家雅各布在《了不起的麵包》一書中提到一些有趣的細節,這種戰爭麵包並不至於無法下嚥,剛出爐的麵包至少還是有一定的穀物香氣,但英國食品部頒布的《麵包令》卻相當誇張,嚴禁銷售新出爐的麵包。此舉是基於兩個考慮:一是麵包出爐後十二小時內不允許銷售,這讓麵包變得梆硬且喪失風味,人們會因此減少食量。二是平時負責麵包生產的是男性工人,他們在午夜就開始製作,這樣第二天一大早人們就能買到新鮮出爐的麵包了。可戰爭爆發後男性大多去了前線,麵包生產的工作多由女性承擔,但女性需要照顧孩子,很難適應黑白顛倒的工作條件,所以改為白天烤製後放一晚再出售,這樣還能省下夜晚照明的電力消耗。
這種情況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發生了逆轉,喬利伍德工藝(CBP)作為一種批量發酵方法,高速攪拌機縮短了製作麵包的時間,不必等待麵團發酵,而是立即烘烤,可以快速生產出美味、柔軟的白色加工麵包。在十九世紀的英國文學中,充滿了用叉子插住麵包放在煤火前烘烤的場景一去不返。據統計,如今八成的英國麵包是使用CBP技術生產的,剩下的百分之十五是透過超市麵包店的其他自動化流程生產的,只有百分之五來自手工麵包店。自此,白麵包變得很便宜,黑麵包卻不那麼便宜了。
在今天的英國,雖然黑麵包不至於只有富人消費得起,但很多窮人確實對五英鎊的麵包望而卻步。有趣的是,按《超加工人員》一書的作者克里斯.圖勒肯的說法,根據官方《英國飲食指南》,英國手工麵包店的黑麵包通常選用有機原料,粗糧比率更符合現代高端膳食主義者的要求,而切片麵包往往鹽和糖的含量偏高。從健康角度講,是不是意味着有關黑白麵包的爭論並未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