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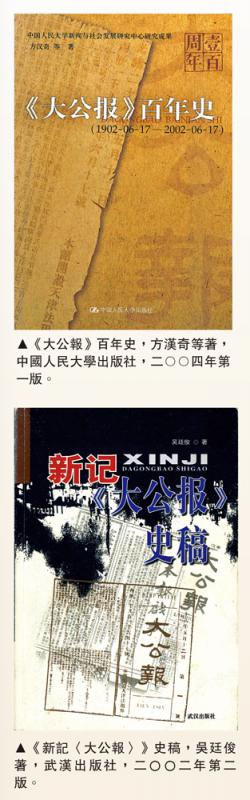
圖:(上)《大公報》百年史,方漢奇等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四年第一版。(下)《新記〈大公報〉》史稿,吳廷俊著,武漢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第二版。
一部新聞史,半部在大公。一百二十年來,《大公報》始終與時代同呼吸,與民族共命運,立言為公,文章報國。報上所刊載的文字,既是當時之新聞,更是今天之歷史,其內容之豐富、涉及之廣泛、影響之深遠,恰如一部近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百科全書。\大公報記者 鄭曼玲
對於史學界而言,研究中國新聞史、尤其抗戰新聞史,《大公報》必定是繞不開的媒介。長期以來,評析《大公報》的書籍文章汗牛充棟,其研究角度方向雖各有特色,但觀點結論卻大同小異│對報章的耕耘、對報人的栽培、對報格的珍視,是《大公報》歷經百年風雨,依舊一紙風行、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而這一「大公密碼」的梳理總結,不僅具有珍貴的歷史價值,對於當今媒體如何肩負使命擔當、緊扣時代脈動、書寫中國傳奇,亦具有不可多得的現實啟示意義。
新聞「四絕」 克盡言責
劉勰有言:「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
不少新聞史學者認為,讀《大公報》的文章,就能強烈感受到這種文字的魅力。當中不少經典作品,筆墨行雲流水、酣暢淋漓,又博而不散、紊而不亂,得以引領讀者神思飛揚,縱橫馳騁,會古訪今。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莫過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大公報》的社評、星期評論、新聞通訊、副刊,被公認為當時新聞界的「四絕」。
首先是社評。新記《大公報》時期,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三人都把社評寫作當作報紙工作的頭等大事,從題目到觀點都須經過共同商量,然後由其中一人落筆,最後再由張季鸞定稿。
就張季鸞的為文風格而言,他是「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這既是張季鸞對自己社評技巧的概括,也是《大公報》文章的一大特色。張季鸞的政論,不偏激褊狹,不任性使氣,其論事析理,穩健明達,不溫不火,如沐清風,如飲濃茶,娓娓道來,入木三分。他不靠筆走偏鋒、嘩眾取寵來奪人耳目,而是以分析的透闢、說理的犀利而名世。
著名的大公「三罵」│一罵吳佩孚「有氣力而無知識」;二罵汪精衛的領袖欲;三罵蔣介石不學無術,皆出自張季鸞筆下。而他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所撰寫的《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呼籲「精誠團結,一致地擁護中國」,更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繼承他衣鉢的王芸生也深得真傳,社評寫得有才氣、有骨氣、有銳氣。中國新聞史學會名譽會長方漢奇在《大公報百年史》中評價道,撰寫社評的諸公個個都是嫉惡如仇、滿腹經綸的好手,使得《大公報》的社評,從內容到文字,始終保持較高水平,受到讀者的重視和稱讚。
其次是星期論文。《大公報》開闢星期論文專欄起始於一九三四年一月,應邀為專欄撰稿的有胡適、傅斯年、梁實秋、茅盾、老舍、沈從文等。與星期論文相配合,《大公報》還開闢了一些學術專欄,錢鍾書的《休謨的哲學》、費孝通的《鄉土重建》等鴻篇巨構,都曾在此發表。
方漢奇認為,星期論文和學術專欄的開闢,極大提高了《大公報》的文化內涵,提升了《大公報》的社會地位,擴大了它在知識界的影響力。
再次是新聞通訊。大公報見證並記錄了諸多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節點,克盡言責,從未缺席,新聞通訊也成為《大公報》的一大特色。范長江採寫的紅軍長征系列通訊,蕭乾採寫的二戰歐洲戰局系列通訊,呂德潤採寫的中國遠征軍系列通訊,楊剛採寫的旅美通訊等,情文並茂,文采斐然,發人深省,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
最後是副刊。《大公報》對副刊編輯向來十分重視。在蕭乾、楊剛等幾位副刊主編的主持下,《大公報》的文藝副刊發表過不少進步的文學作品,也發現和培養了一大批後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地位舉足輕重的作家。
陳白塵的獨幕劇《演不出的戲》、巴金的《「愛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胡繩的《上海通俗化問題之討論》等曾轟動一時的作品,還有楊絳的小說處女作《璐璐你不要哭》,都是在《大公報》副刊上發表的。
一九三六年九月,《大公報》續辦十周年,報社決定設立《大公報》文藝獎。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畫夢錄》、盧焚的《谷》等作品在評選中脫穎而出。
在介紹《大公報小說選》時,王芸生曾寫道,「一個老實的刊物,原應是一座橋樑,一個新作品的馱負者」,一語道盡了《大公報》着力辦好「文藝副刊」的初衷。
群英薈萃 愛國敬業
報人是一家報館最大的財富。對於《大公報》而言,栽培打造一支星光熠熠的記者編輯隊伍,無疑是報紙獲得巨大成功並影響日隆的決定性因素。用人方面向來不計學歷,不問出身,唯才是舉。執掌人事大權的胡政之曾經說過,「不怕你有九十九分短處,只要有一分長處我就能用你」。
事實果真如此。《大公報》許多名記者都並非新聞科班出身,范長江、子岡都沒有讀完大學,徐盈、呂德潤、張高峰在大學念的分別是農業、財會、歷史專業,而朱啟平先是學醫,後來才改行。但他們都熱愛新聞工作,有追求,肯努力,大公報就充分信任他們,放手讓他們發揮所長。
對於記者新丁,《大公報》有個不成文的規則,即內外互調,輪崗培養。記者在地方跑新聞、做外勤,如果表現突出,報社就會將其調回編輯部做編輯工作;一段時間後再外放各地,成為特派員;如若繼續展現出發展潛力,就會被調回報社,晉升為部門主管或業務骨幹。
如北平辦事處主任徐盈,就曾當過重慶大公晚報的要聞編輯、渝版編輯主任;大公報東北特派員呂德潤後來就調到滬版任要聞編輯、台北辦事處主任;抗戰勝利前夕,朱啟平作為特派員隨美國太平洋艦隊採訪,回到上海後就成為滬版要聞編輯。
曾任中國報協書記處書記、《大公報》著名記者張高峰之子張刃在《閒話大公報》中分析,這樣安排的目的,可以讓骨幹人員既懂採編業務,又體會各自甘苦,逐漸成長為多面手。很多記者正是在這樣的栽培磨練中,逐步形成各自風格,成長為名揚天下的記者編輯。
張刃認為,知識分子崇尚個性,講情懷,重志趣,《大公報》人亦不例外。當中,強烈的愛國情懷,幾乎是大公報人所共有的。胡政之、張季鸞均曾留學日本,是知日派,但更是堅定的抗日派。抗戰期間,他們力主「一不投降,二不受辱」,誓言決不在日軍鐵蹄下辦報一天。為了共赴國難,《大公報》六易其館,顛沛於戰亂之中;縱然面對敵機的狂轟濫炸,仍堅持在防空洞中出版,向國人發出倡導堅持抗戰的最強音。
其次,鮮明的大眾情懷,也是多數《大公報》人所具備的。張季鸞朋友多、人緣好,也帶動其他記者形成廣泛的朋友圈。他們憑藉這些人脈,體察民情,洞悉時局,寫出不少反映民意、為民請命的優秀作品。
再次,兢兢業業、恪盡職守,也是《大公報》人的共同特點。張季鸞為人隨和大度,但在新聞稿的遣詞造句上卻尤其「斤斤計較」。胡政之曾說他「在編輯時往往題目一字修改,繞室彷徨到半小時,重要社評無論他寫的或我寫的,都要反覆檢討,一字不苟。重要新聞如排錯一字,他可以頓足慨嘆,終日不歡」。
這種精神多為後來同仁所取法,在對新聞業務精益求精的追求中,不少《大公報》記者都形成了各自的專長:張季鸞堪稱典範的時政評論、王芸生鞭辟入裏的日本問題研究、徐盈精闢獨到的經濟問題分析、子岡膾炙人口的社會新聞、呂德潤引人入勝的戰地報道、朱啟平作為教材傳世的通訊佳作……這些名家專長的匯集,成就了《大公報》版面輝煌。
周恩來總理在談到《大公報》的歷史貢獻時,特別強調《大公報》為中國的新聞事業「培養了很多傑出人才」,而《大公報》也因此贏得了「新聞界之黃埔軍校」的美譽。
報格高尚 風骨猶存
一九四一年五月,《大公報》獲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頒發「密蘇里榮譽獎章」。該獎章被公認為新聞行業最具聲望的國際獎項之一,獲此世界性殊榮,中國報紙只此一家,也僅此一次。
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在頒獎詞中說:「《大公報》對於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之報道,始終充實而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於國內輿論者至巨。《大公報》自創辦以來之奮鬥史,已在中國新聞史上放一異彩,迄無可以頡頑者。」
世界上最古老的新聞學院,與最古老國家的新聞機構之結緣,殊非偶然。中國新聞史學會秘書長鄧紹根教授曾就此撰寫學術報告分析稱,《大公報》能夠一紙風行、傳揚國際,成為首家且迄今唯一獲得「密蘇里獎章」的中國媒體,有其三大原因。
首先,堅守愛國陣地,站在時代前沿。鄧紹根認為,《大公報》自一九○二年六月十七日創刊以來,始終洋溢着愛國熱情,傳播信息,主導輿論,臧否時事。而且為了共赴國難,《大公報》多次搬遷,舟車輾轉,歷盡艱險,實具有「異常之勇氣、機智與魄力」。
其次,專業水準高,影響力大。鄧紹根指出,在當時風雨飄搖的國內外局勢下,《大公報》堅持「文人論政」的傳統,文章報國,身體力行,以天下為己任的襟懷和抱負,關注民族命運和國家興亡,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第三,恪盡言責,堅持抗戰。抗戰爆發後,《大公報》立即義無反顧地成為「百折不撓的主戰派」。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大公報》抗戰到底的態度始終十分堅決,言論中沒有一個字對抗戰的前景發生動搖,也沒有在敵人統治下辦過一天報。鄧紹根認為,一家沒有得到當局任何資助的民辦報紙,能夠堅定地毀報紓難,能夠力扛抗戰到底的輿論大旗不倒,十分難能可貴。
鄧紹根指出,《大公報》獲得「密蘇里榮譽獎章」,即便放在今天,依然有其現實啟示意義。當前紙媒身處蕭瑟寒冬,力求突圍,仍應堅持內容為王,堅守底線,堅持品質,重視社會效益。「中國新聞史上有句名言:人有人格,報有報格,國有國格;三格不存,人將非人,報將非報,國將不國。」鄧紹根認為,報紙應該重視報格,才會受到社會的矚目和尊重,得到讀者的認同和歡迎。這正是百年大公留給當代傳媒業者的啟示及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