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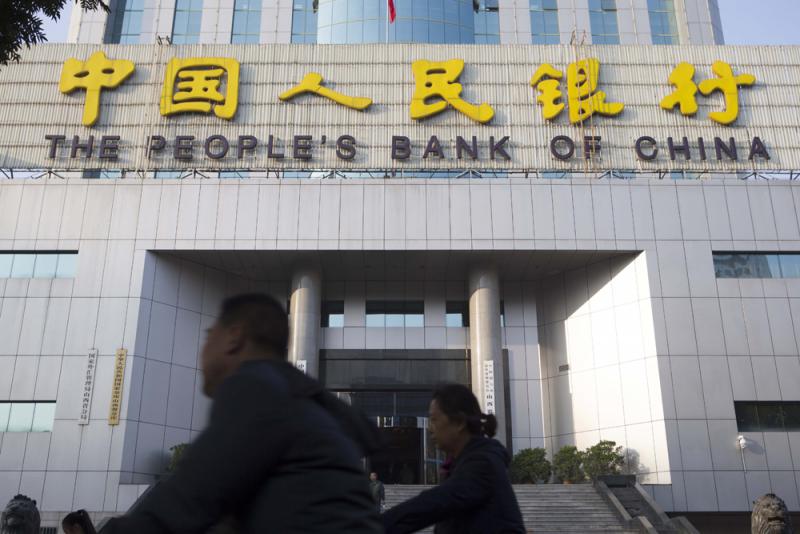
圖:分析認為,此次定向降準與美國加息幾乎前後腳,而且是在人民幣快速貶值之時,表明人民幣匯率在人行決策中的重要性顯著下降\中新社
中國央行上周日(24日)宣布定向降準。此次定向降準與4月定向降準有很大不同,完全釋放增量貨幣,更符合總量政策而非結構政策的特徵,同時不再強調降準的「對沖作用」。\九州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 鄧海清
今次定向降準是對6月20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的具體落實。從以往經驗來看,國務院會議定調定向降準之後,距離落地往往只有一周左右的時間,再次得到驗證。
人幣貶值在所難免
今次定向降準釋放以下四大信號:
信號一:此次定向降準與4月份定向降準有很大不同,此次定向降準完全釋放增量貨幣,更符合總量政策而非結構政策的特徵,同時不再強調降準的「對沖作用」,與4月份更側重置換MLF(中期借貸便利)、對沖貨幣回籠完全不同,驗證了央行貨幣政策確實出現「政策巨變而不是微調」。
信號二:此次定向降準徹底證偽了「貨幣緊縮去槓桿」的說法,驗證了筆者提出的貨幣緊縮是去槓桿的毒藥。貨幣緊縮已經徹底被中國央行拋棄,「嚴監管+降準」才是央行「正確的事」。
信號三:此次定向降準的功能與以往相比有重大變化,增加了降低企業槓桿率的功能─「債轉股」,驗證了筆者提出的「去槓桿將從『劇痛』轉入『無痛』」,這與2018年以來的信用緊縮和風險事件頻發有關。「去槓桿」大方向仍要繼續,但會減少「一刀切式去槓桿」。
信號四:此次定向降準與美國加息幾乎前後腳,而且是在人民幣快速貶值之時,表明人民幣匯率在央行決策中的重要性顯著下降。我們一直強調,「匯率,從來沒有中國很多人認為的那麼重要」,在中美經濟走勢分化、中美貨幣政策分化、美元升值周期下,中國政策層絕不應重演2014至2016年的「棄外儲、保匯率」悲劇,而應當讓匯率市場化地波動,人民幣貶值在所難免。
在降準之外,筆者認為更值得關注的是央行6月22日的《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2018)》。這一報告歷來不會引起市場關注,但是此次報告中有一個重大信息:「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確認了6月20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的流動性基調由「合理穩定」改變為「合理充裕」。
政策層對於流動性基調的變化,是解釋中國貨幣政策、債券市場的不二法門。
2014年四季度至2016年三季度貨幣流動性處於利率低中樞、低波動的情況,這一時期的表述是「合理充裕」、「充裕」,國債收益率在這一時期從4%下降至2.7%;
2016年四季度至2017年三季度貨幣流動性處於利率中樞逐步抬升、高波動的情況,這一時期的表述是「基本穩定」,國債收益率在這一時期從2.7%上行至4%;
2017年四季度至2018年5月,利率中樞略微下行、波動幅度降低,「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穩定」正好介於之前兩個時期,且較前期出現邊際寬鬆,國債收益率由4%下降至3.6%;
2018年6月20日,國務院對流動性定調為「合理充裕」,貨幣流動性將面臨進一步寬鬆,國債收益率將由3.6%變到多少?
十年國債或降至3%
對於降準對債券市場的影響,市場投資者可能吸取上一次降準的教訓,即4月降準後,對債券市場實際上是「利多出盡」,疊加資金面意外緊張、美債上行、油價上行、中美貿易戰和解預期等因素,導致債券市場持續大跌。因此,對於此次降準,市場投資者可能依然按照「利多出盡」來做。
筆者認為,市場這種反應屬於「刻舟求劍」式的學習記憶曲線,忽略了當前與4月份降準的幾大不同:
首先,國務院定調流動性由「合理穩定」到「合理充裕」,央行已經進行確認;而4月降準之後,資金面持續超預期緊張,央行態度並不明朗。
其次,當時中國經濟下行並未得到普遍認同,且證據確實不夠充分,而目前需求端、融資端數據均驗證經濟已經下行,且生產端一方面數據失真,另一方面從高頻數據看也已經回落。
再次,中美貿易戰環境完全不同,當時是中美和解可能性巨大,而目前中美貿易戰已經開打。
最後,外部環境存在巨大不同,4至5月份美債收益率從2.7%上行至3.1%,而目前美債收益率僅為2.9%,原油價格當時市場主流預期破80衝100,而目前原油價格已經回落穩定在70至77區間。
重申2018年「十年國債下降至3%」,筆者在2017年底提出「2018年最好、最確定的機會是利率債」,「十年國債3.8%閉着眼睛買」早已得到充分驗證,之後提出「2018年兩階段行情,第一階段是4%至3.7%,第二階段是3.7%至3.4%」,現在筆者基於中國政策層定調和經濟基本面的變化,認為十年國債收益率將下降至3%。
對於人民幣匯率,依然維持「人民幣匯率貶至7」的觀點不變。匯率已經不再是制約中國央行的因素,在中美經濟走勢分化、中美貨幣政策分化、美元升值周期下,中國政策層絕不應重演2014至2016年的「棄外儲、保匯率」悲劇,而是應當效仿歐洲、日本,允許人民幣匯率在合理水平上進行貶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