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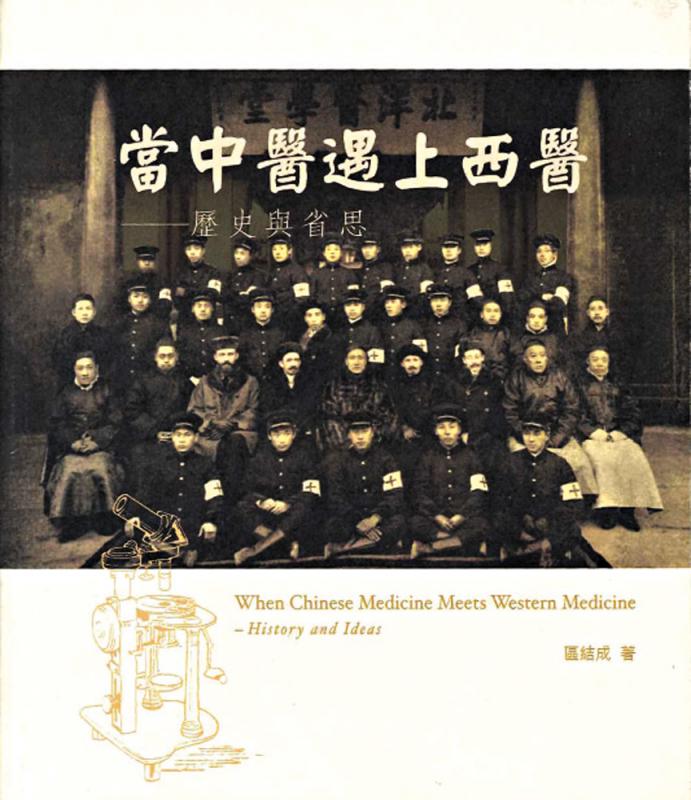
圖:由三聯書店(香港)出版的區結成著作《當中醫遇上西醫》(繁體版)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醫和西醫孰優孰劣的爭論再一次燃起「戰火」。這些年,關於這個話題的文章和著作陸續出版。我手頭有一本《當中醫遇上西醫:歷史與反省》(簡體版書名)出版於2005年,當時恰逢SARS疫情結束不久,此書的寫作緣由之一,正是受SARS之刺激。有意思的是,我也是在那一年完成了研究生學業,畢業論文的研究對象是近代中西醫論爭背景下之1920年代協和醫學生群體。選擇這個題目的緣由之一,當然也是SARS。彼時,我就已讀過這本《當中醫遇上西醫》。此番重讀,又有一些新的感受。
我們翻翻歷史,就會發現中西醫爭論已延續了一百多年,在清王朝、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新中國等不同政治環境和社會制度下,都有過激烈的表現,而且論題大致相仿。就此而言,或許這真是超越歷史語境和意識形態的「醫學」話題,但我們如果細察爭論內部紋理,就會發現「醫學」之所以成為一個話題,恰和歷史語境密不可分。當中醫遇上西醫,作為一個歷史事件,有些人將之視為羊遇上了狼,翻讀20世紀上半葉迄今的醫學爭論文獻,會讀到大量充滿火藥味的語句,即便是一些史學着作,也難免激憤之言。而《當中醫遇上西醫》這本書,最大的特色是理性務實和向前看的態度。這或許和作者本人是醫學專業人士有關。作者區結成,生於香港。喇沙書院畢業後留學美國,獲布朗大學生物學學士、醫學博士。1982年回港受訓及工作。作為一名兼具醫學和文史素養的寫作者,區結成在書中以帶有溫情的冷靜,坦然看待中醫和西醫之間的差異,以及由此而來的爭論。
平心靜氣說紛爭
書中說道,真要探究中西醫學之路,「可能須首先放下西醫的優越感和中醫的歷史心結」。筆者以為,這句話可以視為本書之核心論點。基於此,作者從四個方面展開論述。「歷史篇」追溯中西醫各自歷史及其相遇。「論爭篇」述中醫醫學之論爭,特別是中醫在近代的掙扎求存。「醫學篇」討論中醫學的核心學術主題之現代化。「現代篇」則探討中醫學的發展之路。全書貫通着兩個疑問:「世界上沒有兩種醫學,真正的醫學只有一種?」「中醫學會被現代淘汰嗎?」兩問實質上是一問:中醫在現代社會語境下如何發展?從敘述邏輯看,本書大體按照中醫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敘事線索。而西醫的發展路徑及其進入中國,則構成了一種參照系。本書雖可歸入文化閱讀之類,但材料取捨和引證十分規範,整理了中西醫學論爭史上的重要文獻和觀點,並使之以「對話」的樣式呈現給讀者。
如書名所示,作者採取了從歷史回望現實的理路。中國醫學史的傳統模式是「名醫傳」,進入近代以後,才有線性史觀的中醫史出現。在本書中,作者援引了多部經典的醫學史論述,對中醫史作了極簡的勾勒,指出了一些關鍵性的節點,比如,「在歷史上,中西醫道各有本源,但並不完全相左」,「中西醫學的歷史殊途,關鍵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前後」,「19世紀下半葉是中國失去文化自信的時期」,「中醫真正面臨危機,應是在1894年甲午戰敗之後」,等等。
書中說,19世紀之前,西方醫學順着希波克拉底、蓋倫、維薩留斯一路發展下來;而中國醫學則按照《黃帝內經》、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金元四家,再到吳又可、葉天士、吳鞠通等的歷史道路,穩定而自主地發展,並未受到西醫的衝擊。到了19世紀,情況發生了變化。西方科學一門一門地起飛,帶動醫學出現了飛躍。同時,西醫進入中國,逐漸確立起自己在中土的社會地位和知識權威。中醫在此時也開始認真思考中西醫學的異同。於是,互為「對手」的歷史真正開啟。如作者所指出的:「或許從合信《全體新論》等五種着作在中國流行開始,中醫終於感受到挑戰了。」所謂「合信氏西醫五種」,是指從1851年到1859年,醫學傳教士本傑明.合信(1816-1873)出版的五種醫學着作,包括《全體新論》、《博物新編》、《西醫略論》、《內科新說》、《婦嬰新說》。當時,四川醫家唐宗海(1862-1918)提出了中西醫學「匯通」的觀念;廣東的朱沛文則提出在醫學中,屬於「形」的範圍應「從洋」,而屬於「理」的範圍應「從華」。此後,到惲鐵樵(1878-1935)、張錫純(1860-1933)乃至以後,如果我們不計較概念的表述,中西匯通的努力可以說至今也未停止。
一場官司百餘年
然而,這種為了醫學的努力受到了來自醫學之外的巨大影響,這甚至遮蔽了唐宗海們設計的方案。作者指出,「在甲午之前,唐宗海、朱沛文等人對中、西醫融合的思考,並沒有什麼危急存亡的恐懼。他們以為,只要能在中醫理論體系中設定位置,吸納新來的、年輕的西醫學,便是出路。」甲午戰爭之後,亡國的危機感空前強烈,醫學革新塗上了救國的色彩,中西醫論爭的論題和目的也隨之發生了轉向。隨着西醫院、西醫學校漸成氣候,特別是以余雲岫等為代表的西醫留學生的歸國,更讓中醫的「對手」變得真實而具體。雖然,惲鐵樵還在努力地用西醫的概念註釋《傷寒論》,以期改良中醫;張錫純更是在臨床基礎上倡導「衷中參西」,但不論從救亡圖存的話語強勢而言,還是從現代學術的全球網絡和對話機制來看,這些努力都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和社會支持。
作者在書中專門探討了科學共同體在醫學發展中的作用。應該說,這是以往醫學史中關注較少的。書中以中國科學社等學術社團的成立為例,指出「教育制度與課程改革之後,西方的近代知識與科學方法幾乎全盤取代了傳統的經史詞章為本的知識體系。中國的學術進入了『後經學時代』。」更有直接關係的,當然是中華醫學會在1915年的成立,這個延續至今的學術組織,從誕生以來就在為現代醫學在中國的發展作貢獻。相比而言,中醫在這方面比較滯後,雖然也有中國醫學會等組織,但組織鬆散而且內部凝聚力薄弱,在中醫共同體建設方面收效不着。
醫學史的梳理,佔了本書的一半篇幅。對於醫學歷史而言,這當然是極簡的,不過,作者抓住了這段歷史的關鍵節點和變量,就像一位高明的畫家,寥寥幾筆,計白當黑,描繪了中西醫學在中華大地上此消彼長,特別是中醫從自信和主動轉為被動的歷史圖景。而這一轉折,又離不開中醫的核心理念及世界觀在近代的跌宕命運。
革新再造路漫漫
醫學史家昂斯丘爾德說過,在任何社會一種醫療方法體系的強弱不僅是繫於它本身的客觀療效;同樣重要的,是社會政治群體的理念,是否容納這種醫療方法體系背後的世界觀。這段話對於理解中醫的命運極為重要。以我們的日常經驗來驗證,中醫的療效誰都看得到,但它何以有此療效,能說清楚的人卻不多。
本書對五行學說、針刺療法以及中醫的「臟像」、「證」等核心概念作了專門分析,特別是介紹了歷史上關於這些問題的重要觀點,從而給讀者以比較、選擇的基礎。「證」和「臟像」是中醫十分獨特的概念。「辨證論治」更是被認為中醫最重要的特色之一,甚至作為中醫區別於西醫的標識。作者對「證」作了比較詳盡的分析,並且反覆強調,從理論上和實踐上把握這一概念都不是容易的事。為此,書中還專設一節「回歸病案看『證』的生命力」,結合一位頭痛症病人的診治過程,說明中醫辨證施治在臨床上的靈活應用,及其與西醫的差別。以筆者的閱讀體驗而論,若作者非醫學專業人士,對此類問題的分析恐怕難以如此通透。由此也可想到,中西醫學論爭雖為一社會歷史事件,若真要讀懂弄通其要害所在,醫學史之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恐怕缺一不可。
與中醫理論和概念相較而言,針灸無疑更加「接地氣」,也更具生活感。作者在書中區分了針刺學和灸法,認為中醫針灸與西醫學接軌的進程比中醫其他方面要快。西醫裏面的康復醫學、疼痛醫學、麻醉學已接受了針刺療法,灸法則仍被擋在門外。因此,「雖然中醫的針刺學在西醫結合上面仍有不少未解決的問題,但大體而言,針刺療法已不再需要常為未來的存亡問題而焦慮。」在追溯針刺的歷史時,作者再次說明針刺放血是古代醫學共有的手段,實際上也從一個側面回應了貫穿全書的「一種醫學還是兩種醫學」的問題。書中還着重分析了經絡學說和針灸臨床上的「錯位」:對「腧穴」的掌握和運用更加受重視,而經絡學說卻有門庭冷落之虞。在筆者看來,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有力地說明對於醫療實踐而言,「療效」、「管用」確實是硬道理。
按此思路推論,自然提出了中醫究竟該如何發展的問題。本書的最後一個篇章,探討的正是這個問題。作者首先分析了兩種醫學強調各自特色、按特色發展的思路,特別是「西醫辨病、中醫辨證」的思想,他引述了一些中醫對於強調各自分工和特色這一思路的擔憂,指出按此思路看似中西醫互不干擾,但「只能有助雙方初步地互相理解,並不能督促中醫學更上一層樓」。進而又援引西方醫學史上「順應療法」等「另類醫學」的命運,說明「多元並存」其實並不能給中醫的發展提供真正的保障。他還直言不諱地指出,中醫學對現代醫療的可能貢獻,固然不應止於「補足及另類醫學」,但祈求設計出一種新的平分秋色地結合的未來醫學模式,在現實的醫療處境中恐怕只能落空。西醫學在現代與可見的未來都是由實證醫學與創新科技所推動的,它不會整體地思考「新的醫學模式」。科學與科技的能量很大,不會騰出什麼空間由中醫推動根本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現代西醫學的思維有「系統論」的成分,傳統中醫學有樸素的系統論的洞悉,這都沒有說錯,但西醫學不會採納以陰陽五行經絡腑臟學說為本的中醫學說。
那麼,中醫的前途究竟在何方呢?作者認為,中醫應該回應「速度」和「過硬」的挑戰,勇於自我變革。但是,「整體而言,中醫學並未能得益於現代科學方法與相關科技的巨大能量,為自己的發展加速或更新。」同時,對於「循證醫學」的崛起和流行,中醫也缺乏必要的吸取和回應,這造成其在嚴謹性得不到應有的提高。看得出來,作者對中醫是充滿期待的。用他的話說,對中醫能否「通過科學的關口,登上一個現代醫學較接近的學術平台」這一問題,他抱有樂觀積極的答案。
考諸歷史,「中醫」之名,本是應對西醫進入中國而生。在中國的歷史、制度和文化語境下,中醫的發展離不開西醫,西醫的發展又何嘗能離開中醫。行文至此,想起張載提出的「有像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中西醫學這場「官司」打了一百多年,在既定的中西甚或古今的思維框架中,大概很難得到終極的答案。以筆者淺見,在個體求醫療治或醫者治病救人之層面,昔日章太炎倡導的「以療者之口為據」極為務實而有效,而在宏觀的醫學理論或醫事制度建設層面,則有賴於人類多元文化之進一步交融發展,以及命運共同體之實現,方可能有終極解決之道。無論就哪一層面而言,本書所表達的理性態度,以及提供的醫學和歷史知識,都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一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