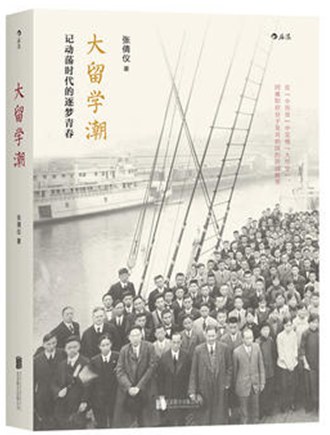明末清初的大儒顧炎武曾對友人論及為學著述之道,「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採銅于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這段話的大意是,有的人寫書多作「二傳手」,摘抄他人舊說,而正確的做法應是「採銅于山」,從一手資料出發,成一家之言。張倩儀所著《大留學潮:記動盪時代的逐夢青春》,可謂一部採銅于山的力作。
尼 三
為寫此書,作者張倩儀搜羅了三百馀位二十世紀上半葉留學親歷者的回憶錄,從中爬梳近代留學史的大量生動細節,按留學大潮起落之邏輯,從留學生求學、打拼的不同側面娓娓道來,「立體式」地再現了二十世紀上半葉那一股「三千年未有」的留學大潮。
出發與歸來
今人治學,多倡「問題意識」。然而,真正的問題意識必然是「土生土長」,也即內生于論題本身之中的,一項研究或一本論著,只有探究符合論題自身邏輯的「問題」,才有真價值。那些單純從理論演繹出來的「問題」,則難免陷入凌空虛蹈、人云亦云的境地。《大留學潮》是一部構筑在大量生動細節之上的史著,別開生面、文辭通達、曉暢好讀,且不乏細膩的故事,但這并不妨礙其學術邏輯的清晰,與關注問題的質樸。在我看來,也正是這一點,使它比一般的歷史作品更耐讀。

一九一八年赴美留學的清華學生在上海登船 書中圖片(選自《清風華影》,清華大學出版社)
本書第一章「出國的雄心與現實」探討的是為何留學的問題,接下來,「錢從何處來」「初出國門」「大潮第一波:‘留學東洋’」「大潮第二波:‘新大陸新風氣’」「大潮第三波:‘歐陸的特殊浪潮’」「學習」「生活」「歸去來兮乎」等幾章,分別回答了留學經費、路徑、去向、生活、學習以及學成歸國等諸問題。顯然,這些問題是當我們把目光關注到留學大潮時自然會想到的,而不是從某種教育學或文化傳播理論中生發出來的。而作者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也恪守了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材料之外「一點也不越過去說」(傅斯年語)的治史態度。《呂氏春秋》有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史學研究的道理其實也一樣,沒有哪個留學生的回憶系統地回答過今人關心的留學史上的問題,但《大留學潮》以三百多種回憶史料完成了集腋成裘的工作,把一幅基本完整的近代留學史拼呈讀者。
比如,關于為何留學的問題,《大留學潮》將其歸結為幾種「夢」:一是鍍金夢,只有出洋鍍過金的人才能當「洋進士」,趙無極的回憶錄中說,不出國鍍金,無法當大學教授,只能當講師。楊絳回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那時候的社會風尚,把留學看得很重,好比‘寶塔結頂’,不出國留學就是功虧一簣。……我親眼看到,一位同學聽到別人出國而自己則無份時,一時渾身發抖,眼直口呆,滿面流汗。」二是救國夢,吳文藻就是「帶著學西方和教育救國的理想,赴美留學」。郝更生的回憶說,五四之后「留學生所想的,幾乎一致的是如何學些對于國家民族有用有益,對于解救國家民族有效有速效,最好能立竿見影、根本解決之效的學問,然后早日回國,將所學能貢獻于祖國。」而救國的理想,又可細分為科學救國、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經濟救國以及后來成為一股最有力浪潮的革命救國,本書對此都有揭示,使讀者對那一段歷史的認識更加有血有肉。
再如留學生的歸國及其面臨的困境。魏壽昆的回憶錄中說,「學者和技術人員,終是兩種人才。在歐美大學只能去求學,技術上的知識得到很有限。不過這在歐美學生,沒有妨礙;茍愿投身工業,則畢業后可入工廠,在極短期內便能得到工廠內應有的學識和經驗。而在中國則不然,留學生回國后,非但無工廠可入而得重事深造,還要努力去創工廠,這點可見我國留學生處境的困難。」本書作者感嘆道:「傳統的進士大都是文人學者,被譏笑為百無一用的書生,誰能料到抱著實用救國目的的洋進士,竟然也主要是在文化教育界發揮所長呢?」讀書至此,筆者也不禁嘆息,此種困境似乎至今尚存,這或許也是讀《大留學潮》可以得到的鏡鑒之一吧。
代際與國別
《大留學潮》涉及的三百多部回憶錄的傳主具有廣泛代表性,其所學專業、留學性質等各不相同,但最重要的,還是代際和留學國度的差異。從時間跨度看,《大留學潮》所取材的回憶錄傳主包括近代最早的留學生之一容閎,出生于一八二八年,一八四七至一八五四年留學美國耶魯大學,也包括一個世紀之后出生、踏上留學之路的許靖華,出生于一九二九年,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三年留學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從留學國度看,則涵括了日本、美國、俄國以及法國、德國、意大利等東西洋強國。而我們知道,在近代留學史和政治史的語境中,代際也好,國別也罷,往往是與政治傾向和派系聯繫在一起的。一部近代中國史,在某種意義上恰是一部不同國度的留學生之間的代際博弈史。如作者在書中所言,后浪推前浪成為一種時代的常態。「不細辨歷史的人,會認為留學生的對立面就是那些抱殘守缺的舊派人物。他們忽略了一個現實,即半個世紀的留學潮已經教育過好幾代新人了。舊一代留學生回來,未及改變中國,新一代留學生又已受新思想而回國……中國出現一代革一代之命的局面,哪怕取過西經回國的留學生,也會被下一代視為保守而揚棄。」十九世紀末敢于抗婚、二十世紀兩度留學的新女性楊蔭榆,就在「五四」之后,成了年輕人眼中的「保守派」,徐志摩說:「中國人見了沒有一個不說他是國粹保存家。」
不同的國度所塑造的留學生群體的思想之別、「主義」之爭,更是早在當年就已經受到關注。一九二○年末,就有人認為,留美學生造成資本主義,留學勤工儉學生造成勞動主義,而留德學生有自然與法國留學界連絡之勢,將來這兩種主義在中國必有短兵相接之一日,造成社會的革命。實際上,二十世紀的世界,已經發展出一個思想與文化全球流動的網絡,即便同在一國留學的群體,也可能被不同的思潮捕獲。后來的新中國元帥聶榮臻在回憶錄中就說,一千多名留法勤工儉學生的社會思潮基本上可以分為五大派:共產黨、國家主義派、無政府主義派、社會民主黨、國民黨右派。學生們不屬這一派,就屬那一派,幾乎沒有一個「白丁」。而據其他史料記載,不同派別的留學生在海外除了論戰不休外,還不惜老拳相向。隨著留學生返回國內,此種海外恩仇也延續下來,對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的政治格局發生了重要影響。比如,主張國家主義派的法國留學生曾琦、李璜為抗衡共產主義思想,一九二三年底成立中國青年黨,并于一九二四年將其總部搬回中國,而在此后幾十年的政治風云中,他們一直「堅定地」站在中共的對立面……
平視與內窺
毋庸置疑,在近代中國這個趨新的社會里,留學生是一個閃著金光的群體,這三個字是「洋氣」「新知」的代名詞,有時還是優勢地位和身份的象徵,比如地處內陸的甘肅曾將到外省求學者一律稱為「留學生」便是一例。近代留學史的論著并不能算少,但重點都在宏觀概述或偏重于教育史、政治史或社會文化史視角,對留學生作為普通青年的日常生活,系統的研究并不算多,有的作品則因文學性過強而淪為捕風捉影的奇聞軼事。《大留學潮》則以平視的態度,探討了留學群體的日常世界,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比如,中國留學生在海外以中國為研究題目取得學位,這在當時就引起過爭議。魯迅諷刺說,有的中國留學生在國外用老子和莊子謀得了博士頭銜,令洋人大吃一驚;然而回國后講的卻是康德、黑格爾。季羨林以此為鑒,決意不步其后塵。《大留學潮》佔據廣博的材料,作了理性平和的分析。作者認為:「一竹竿打到所有寫中國題材論文的人是混學位,也未必無冤情。除了胡適,后來做了大學者、一生勤于研究的留學生,如老一輩的吳文藻、李濟,晚一輩的吳于廑,以至吳文藻的學生費孝通、林耀華倒也都是以中國題材做的論文題目。」又說,「再從當年中國留學的現實情況來看,不少留學生出國時既然滿懷救國激情,那么研究什么對中國有利,恰是他們學習的動力。」比如,法學家王鐵崖就表示對條約問題有興趣,劍橋大學講座教授感到奇怪,問他原因。他說:「道理很清楚,中國受帝國主義壓迫,國際法在中國并無實際效力,在中國對外關系中,重要國際法問題是廢除不平等條約及所引起的種種問題。」
同時,該書還採取從內向外看的視角,以留學生的眼光看待外部世界,集中展示了留學群體作為「文化楔子」的意義。留學生身跨兩種乃至多種文化,首先是插入留學國度的一個楔子,初到異國的他們與那里的文化、民俗格格不入,等到留學日久,漸染洋俗,回到國內時,卻又與國內的環境不太融洽,成了另一種「楔入者」。比如,陳鶴琴回國后,坐船從上海到天津,發現高級艙內也有老鼠,同艙之人也不講公共衛生,「初回國的我看了實在不習慣!」而比日常生活的觀感更深刻的是留學生心中老懸著兩把尺子,如蔣夢麟所說,在美國時,他喜歡用中國的尺度來衡量美國,回國以后,則顛倒過來。書中揭示,對于大多數留學生來說,平衡這種文化落差的,保持人格完整統一的,則是拳拳愛國之心,這也是讀《大留學潮》最令人感動的地方。侯外廬在《韌的追求》中說,妻子臨產,沒錢進私人醫院,只得送公立醫院,而法國公立醫院出生的孩子必須入法國籍,這樣兒子就成了法國國民。一九三○年回國時,法國政府不給他的兒子發離境證書,經法國共產黨朋友幫忙,才把兒子帶回國。對比今日很多國人爭入外國籍,怎不令人唏噓感嘆。本書作者訪問何炳棣時,何先生也表示自己無法忘卻父母之邦,而對比自己成長所得,又感到對中國老百姓有一種罪惡感。
我想,不去父母之邦,動盪不移其志,這就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氣節與情懷,縱然遍染歐風美雨,也不會更改分毫,這也是近代中國歷經劫難卻終于浴火重生的最深層力量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說,一部《大留學潮》又何嘗不是一段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