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 三
前不久,有條「丟書大戰」的微信廣為流傳。據說把書丟在地鐵裏,有助於促進書的流轉以及公眾讀書。不過,我覺得這更像個噱頭。讀書是一種生活方式,喜歡讀的便自行讀去,不愛讀的也不必勉強。但既然拿起書來,就需認真,大眾閱讀或學術閱讀,皆是如此。
那麼,如何才算讀書認真呢?前賢對此多有教誨,朱熹老夫子說:「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仔細,心眼既不專一,卻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亦不能久也。」近代革命老人徐特立則說,「不動筆墨不讀書」,這或可概括為「筆到」,這樣說來,讀書應有「四到」。葛兆光的《且借紙遁:讀書日記選(1994-2011)》可謂這「四到」讀書法的一部好教材。

學者葛兆光 網絡圖片
《且借紙遁》共收書三百餘種,據葛兆光自述,是從「上百萬字的讀書日記中選出來的」。可見,這只是他所讀書之冰山一角。他還說,這本書收錄的多是「並不用心讀」的「閒書」,是一個以學術為業者的「業餘愛好」,解悶消遣之物,和《封神榜》裏的神仙「土遁」或「水遁」一樣,以此之故,書名喚作「紙遁」。其實,這些所謂「閒書」卻是一水兒的學術書,並非休閒讀物。這讓我想起一九二三年胡適為清華學生擬過一個「最低限度」國學書目,一下子開出一百八十四種,被輿論認為太多太專深,而不合乎「最低限度」四個字。葛先生的「閒書」大概也應作如是觀吧。
閒書並不「閒」
這三百多種書中有當代學者著述如周質平的《胡適論叢》,有前賢之作如錢穆的《中國學術思想文叢》,還有史料書如孫寶瑄、翁同龢等的日記,有國人作品,也有西洋人或東洋人的作品如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大部分均為新出版的書,卻也還有些「舊書」如季鎮淮著《司馬遷》(出版於一九六○年)等。總的來看,這些「閒書」即便處於葛先生學問體系之外圍,也沒有超出其治學專長之外,這也可見閒書不「閒」。
更值得注意的是,收入《且借紙遁》的書,一多半出版於境外,又有不少是日文著作。縱然身處開放社會,今天的年輕學人讀到這些書並不太容易,對於僅對學問有興趣而非以此為業的閱讀者,就更是如此了。因此,如我猜測不假,葛先生編選此書時,或也有這方面考慮。不管怎麼樣,這本書都為我們了解全球學術版圖打開了一扇窗戶。
學術之後廚
葛先生可謂著作等身,如果說讀他的其他著作如品味一道道大餐,那麼,《且借紙遁》則是給我們展露了學術的後廚,令後學窺見治學之門徑。
葛先生說,三十多年前,他在北大古典文學專業讀書,專業要求模擬《四庫全書總目》,對所讀書作六百字的提要,「現在回想,這一近乎刻板的訓練,讓我至今總是習慣於對書作『撮要』、『概述』或『摘錄』」。這項功夫正是傳統學人看重的目錄學。鄧廣銘說治史有「四把鑰匙」,其中之一就是目錄學。陳垣也一直強調,目錄學是學問之基礎。我想,如把學問比作多層大櫃子,目錄學好比是抽屜上的把手,為人們拉開抽屜,取出櫃中之物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是,對於學者個體而言,由於術業有專攻,這些「把手」必須手造,無法假手於人,而傳統或現代的各種檢索手段,最多只能充作製造「把手」的工具,絕不能替代「把手」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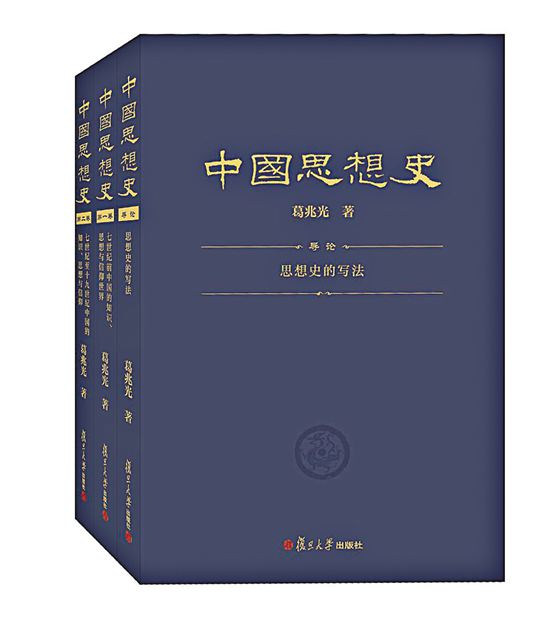
《中國思想史》(復旦大學出版社,二○一三年六月)是葛兆光最負盛名的著作 網絡圖片
捧讀《且借紙遁》,「把手」可謂比比皆是。比如,讀《桑原騭藏全集》的筆記中說,有兩篇有關中國的書評值得一看,一篇論陳垣之《元西域人華化考》,另一篇則論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又如,在陳榮捷(Wing-Tsit Chan)《近代中國的宗教趨勢》(Religious Trends in Modern China)的筆記中,葛兆光說「這部書不僅比尉遲酣(Holmes Welch)三卷本《中國佛教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Chinese Buddism 1900-1950),脈絡更細更清晰,就是與一些晚近才出版的國內有關現代佛教史的書相比,似乎也好得多。」又說,「當然,陳觀勝《佛教與中國社會》一書,亦值得注意。」再如,讀《陳垣來往書信錄》的筆記,提到陳垣與胡適關於《四十二章經》的討論,並指出研究這個問題,還應注意陳寅恪的觀點,以及周一良、周叔迦關於《牟子》,季羨林《浮屠與佛》等一系列論文。類似札記雖只數語,卻已構成一篇論文之基本思路。
治學的心路
此外,書中還有一細節,也有金針度人之效。葛先生的每一則讀書筆記,不論長短均詳載所讀之書的出版年代、出版單位及版次等,凡有摘引皆標頁碼。正所謂磨刀不誤砍柴工,這些貌似細碎繁瑣之處,其實關係治學習慣之養成,值得讀者借鑒。
葛兆光書中有一則讀《胡適日記全編》的札記:「胡適日記中還有許多值得注意的東西,包括他日常讀書所抄錄的一些資料和記下的一些想法,其實,很可以從這裏推測他有關中國歷史的思路。」我們讀《且借紙遁》,又何嘗不能從中體味葛兆光的治學心路,以及他心中那個龐大交錯的學術網絡建構之脈絡呢。
比如,我們可以看到葛先生從不同側面對一個學術主題的反覆關照和映證。讀孫寶瑄《忘山廬日記》時,他發現,孫寶瑄對常識產生了懷疑,這使孫注意到經典之外的資源,於是,中學、西學、佛學在孫的腦中互相比較和詮釋。讀《翁同龢日記》(第三冊、第四冊)時,他又發現,當時中國處於多事之秋,而翁同龢的日記卻表明,中國士大夫依然在傳統生活軌道上緩緩滑行,除了官場公務,仍沉湎於吟詩作畫、搜集字畫、訪僧問道的雅事之中。這兩則筆記指向的都是知識分子精神世界中不太為人關注的部分,用葛先生最負盛名的著作《中國思想史》中的話來說,「在實際的歷史生活中起作用的那些一般的普通的知識和思想」。
微評起毫光
作為讀書日記,《且借紙遁》以摘錄及概要為主,但充滿情趣的微書評也有不少,思想的毫光時有閃現。葛兆光對簡繁《劉海粟傳》的評論,「這真是一部奇書,簡繁是劉海粟的學生,登堂入室,他筆下的劉海粟的為人與作風,讓人想及《笑傲江湖》之任我行,其晚年行徑,讓人想起《將軍碑》中之老將軍,而早年事跡,則讓人覺察二十世紀中國之亂世濁流」。我想,讀過簡繁此書的人,應該都會默默點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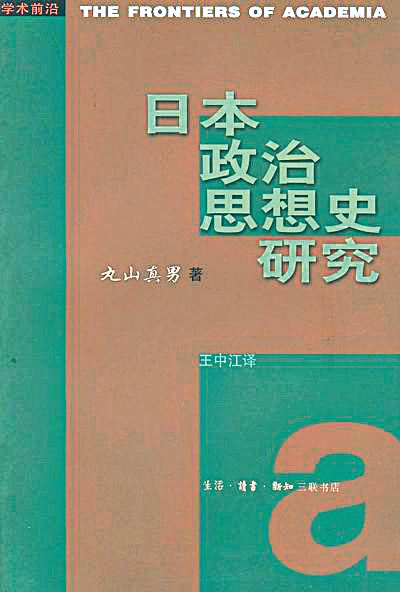
收入《且借紙遁》的書,有不少是日文著作,如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網絡圖片
在子安宣邦的《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讀書筆記之最後,葛先生說:「現在我最擔心的:一是中國學者因為追逐潮流嘩眾取寵而亂跟時尚,完全不考慮具體的歷史語境;二是在對話中失去立場,而被對手同質化,從而成為應聲蟲甚至是跟屁蟲;三是因為『影響的焦慮』和『權力的聲音』而結成朋黨,更黨同伐異、互相亂捧,變成小圈子主義。」這段話寫於二○○六年三月四日,倏忽十年已過,今日讀來,仍有針砭時弊之力。
讀陳雯怡的《由官學到書院》一書時,葛兆光又對當下書院、私塾研究中把書院教育想像得過於完美的情況作了批評,他指出,書院不可能脫離古代中國的環境,不能等同於西方的「大學」,「切忌把來自現實的期待和批判投射到對書院的想像中去。」、「借題發揮批判現代教育是可以的,但是,有不要因為現在教育狀況令人不滿,因而把書院硬拉到『現代性批判』、『西方學科制度批判』之類上去,以至於對於書院教育本身有太多非歷史的評價」。這一觀點實際上也超出書院研究本身而具有方法論的意義了。
在本書的《小引》中,葛兆光還對當下的讀書風氣作了批評:「近來讀書的風氣漸變,不是太實用,就是太草率。實用者好像帶了既定目標匆匆到超市購物,從貨架上揀了自己需要的那幾樣東西,匆匆直奔收銀台,銀貨兩訖便揚長而去。草率者則彷彿在網絡上撒網打魚,憑了幾個『關鍵詞』就漫天鈎去,不管三七二十一,串起來就算,全不顧前後左右語境。」這段話說得生動又深刻。他以書之存在形態不同,將讀書分作幾個時代:「只有簡帛而沒有印刷術語的時代,人們只好鈔書,這時讀的書不僅記憶深刻,常常能讀透紙背的意思」,等到雕版印刷術發明,書肆成為知識的淵藪,遇事查書成了常見的方式,到了鉛字時代,依託圖書館和學術分科制度,查書也劃分了畛域,有了互聯網之後,紙筆束之高閣,考索全靠網絡。
當然,真正影響讀書方式的,是讀書人對書以及讀書的態度。不然,何以在這個「檢索」、「剪貼」的時代,依然有如葛兆光般「笨拙」或「執拗」的讀書者呢?而他的讀書生涯又告訴我們,在讀書這件事上,唯一的捷徑就是一本一本老老實實地讀下去。既然如此,不妨讓我們跟着葛兆光一起回到讀書的「簡帛」時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