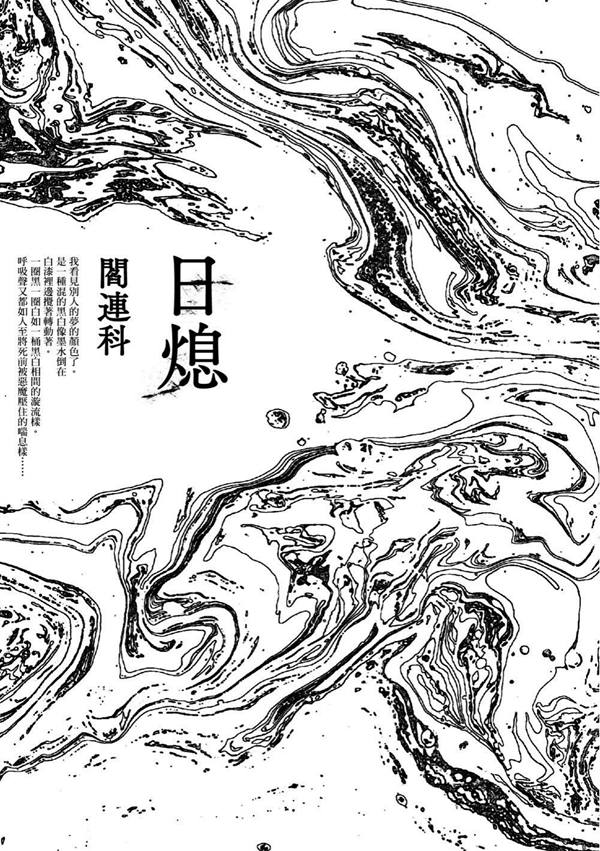大公報記者 管 樂
跟閻連科做訪問的時候,可以明顯地感受到他的焦慮:對寫作狀態的焦慮,對社會現實的焦慮。正如他九月二十二日在香港獲頒第六屆「紅樓夢獎」首獎時於得獎感言中所流露出的對文學創作的焦慮:「作家與文學,在今天的中國,真是低到了塵埃裏去……我們不知道中國的現實,還需要不需要我們所謂的文學,不知道文學創作在現實中還有多少意義,如同一個人活着,總是必須面對某種有力而必然的死亡。存在、無意義,出版的失敗和寫作的惘然,加之龐大的市場與媒體的操弄及權令、權規的限制,這就構成了一個作家在現實中寫作的巨大的卑微。」

閻連科是中國文壇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 大公報記者管樂攝
自我揶揄文學獎「陪跑者」
上一次記者見閻連科,還是在兩年前的香港書展上。那時他剛剛獲頒「卡夫卡文學獎」,是繼村上春樹之後第二位亞洲作家獲此獎項。才兩年過去,當時銀髮中還摻雜着些許黑髮的他如今已是滿頭白髮了。深藍色的短袖襯衫,略顯皺巴的白色休閒褲,單憑外表,要是不曉得閻連科是中國文壇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很容易將他歸類到機關幹部裏,當然,職級還不是很高,因為他臉上沒有那種習慣被奉承的高傲或是讓人產生疏離感的和藹。
儘管閻連科曾自我揶揄在國際各類文學獎中是「陪跑者」─在今年五月公布的二○一六年度國際布克獎中惜敗於韓國女作家韓江,即將於本周內(十月十三日)揭曉的二○一六年諾貝爾文學獎,他再度登上博彩公司公布的賠率名單榜,排位較去年首度入榜有所上升,位列第三十九─其實他早就獲得過多個文學獎項,包括:第一、二屆魯迅文學獎,第三屆老舍文學獎,馬來西亞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卡夫卡文學獎,日本「推特」文學獎,等等。今年七月,他憑藉長篇小說《日熄》獲得第六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首獎,獎金數(三十萬港元)在華語文壇中僅次於茅盾文學獎(五十萬元人民幣)。

放棄宏大敘事只講一晚
《日熄》的故事發生在伏牛山脈中的皋田小鎮,以一個名叫李念念的十四歲少年作為敘述者,講述農曆六月六的酷熱夏夜,幾乎全鎮的人們一夜間集體患上了夢遊症,他們在夢遊裏互相廝殺、搶劫,每個夢遊的人在現實裏不願吐露的、潛藏在內心的慾望卻在夢遊時和盤托出,人性的善惡在昏睡不醒中表露無遺,整個社會的秩序混亂失靈了。夜越深,夢越荒唐,夢遊中的人們以為回到明朝,追隨李自成後裔,要效仿李闖王式的起義發動鎮戰,猶如倒退回蠻荒時代。
用閻連科的話說,《日熄》這部作品「寫得非常辛苦」,是「最艱難的一次創作經歷」,修改了無數次。與以往的作品不同,在《日熄》中,他擺脫了歷史長河,放棄了宏大敘事,只講一個小鎮、一個晚上的故事。
「以前我的小說故事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宏大敘事,有時代,有歷史那條河流,故事基本上沿着那條河流走來走去,是有一個框架的。但是這一次我希望自己的寫作能夠擺脫一個宏大的敘事,能夠擺脫歷史的河流。」在閻連科看來,寫作長篇小說,時間是非常重要的,「往往時間就是那個故事的線索,人物的命運和時間是相聯繫的。我們寫一個人的一生,大多是從這個時間段開始,到那個時間段結束,是很長的。你寫一個晚上,就不可能包含着一個人一生的事情,它就是一個晚上的事情,會讓你的小說發生很多寫作上的變化」。而「夢遊」就是他找到的敘事方式:從睡覺開始到第二天太陽出來結束,一更至日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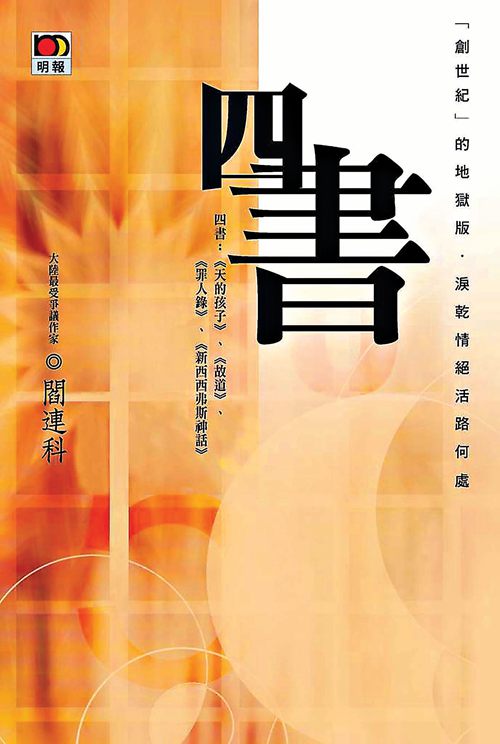
《四書》(明報出版社,二○一○年) 網絡圖片
修改十次以上直書人性
在閻連科以往的作品中,總能發現將虛構人物與真實歷史事件相結合的敘事方式,比如,《年月日》、《日光流年》、《四書》的故事背景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災害,《炸裂志》講述的是改革開放後中國村落的三十年變遷,《堅硬如水》有「文革」的時代背景。而這次,他有意嘗試全新的創作手法,不再試圖將寫作與歷史結合起來,而是真正進入個人化的敘述,更為細膩地直寫人物的內心。
也正因為此,《日熄》經歷了十次以上的修改。出版前改了七、八次,台灣麥田出版社去年十二月初版後,又改了四、五次,「如果現在看一遍,我想還會再改」。
雖然故事的主要人物是敘述者李念念一家,然而過了一段時間,閻連科發現,「除了主要人物,修改都在次要人物上」,要讓「次要人物都豐富起來」。
在修改的過程中,他向身邊的作家朋友、學者教授請教,還在自己任教的中國人民大學創造性寫作研究生班上將作品拿來與一群八十後、九十後的學生一起討論研究。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劉劍梅在看後曾直言小說「過於黑暗」,為此閻連科在後來的改動中加入了很多更為美好的東西,讓「善的一面,或者光亮的一面,在每一個小人物身上都有所加強」。比如,夢遊中有個人物去偷盜神像,偷之前他燒了炷香,還跟別人說,我不是偷是去請的。

非效仿魯迅喚醒昏睡人
紅樓夢獎決審委員會主席鍾玲在給閻連科的頒獎詞中,評價《日熄》「在對人性深刻的描寫上,在對心理層次的處理上,在善與惡的對峙上,都寫得驚心動魄。」
小說最後,李念念的父親李天保在夢遊中以自焚的方式燃起熊熊大火,取代日頭,喚醒了昏睡中的人們,恍若救世主般。「其實他後悔了。」閻連科對記者解釋說。他在小說中寫道:「(我爹,即李天保)朝油坑外邊急急挪着,像要掙着身子從火球裏邊逃出來。隨着那掙的逃的火團兒,傳來的是爹那撕疼死痛轉着身子的嘶喊着─我醒啦。─醒啦。」
關於「救贖」與「抗爭」,魯迅在作品中也表達過無望,但仍會讓讀者看到從無望中得救的希望,在生死輪迴的悲劇宿命中感受到一絲溫暖。美國杜克大學副教授羅鵬在《日熄》的序論中認為,小說與魯迅的《吶喊》有相似之處,都在試圖將「昏睡的人」叫醒。閻連科卻表示,這是他寫作之前沒有想過的,「我只是希望這樣講故事的方法,講一個不一樣的故事,寫出一些不一樣的人的內心世界。當一部小說寫到人的內心,寫到人的靈魂中,它是會給很多人一些新的想像的。」
代入小說自嘲「江郎才盡」
相較於多數作品,作者總是隱藏在故事背後,把控着故事的發展和走向,而在《日熄》中,閻連科直接參與到文本中,他是敘述者李念念的鄰居。念念把自己從黑暗中看到的一切講給鄰居閻伯,希望他可以把這些寫成一部小說。
這是繼《炸裂志》後,閻連科再一次將自己寫進故事。然而,與《炸裂志》中那個自信強勢、用一種不屈不撓的態度推動自身價值判斷的「閻連科」不同,《日熄》中的「閻連科」成了徹頭徹尾的失語者,從講故事的人淪為被敘述者。在李念念眼裏,閻伯「對他的寫作絕望了。對活在世上不能再講故事絕望了」,「我知道他江郎才盡了。腦子乾枯了。寫不出他要寫的故事了。」小說最後,即便閻伯在目睹李天保以自焚的壯烈舉動完成對夢遊鎮民和自我的救贖後,還是因為寫不出故事而出了家,「黃袍光頭,微胖安詳」。

《炸裂志》(台灣麥田出版社,二○一三年) 網絡圖片
對現實的焦灼貫穿寫作
閻連科告訴記者,焦慮始終貫穿在整個創作的過程中,直到小說完成之後,才有所緩解。其實,縱觀閻連科的作品,無論是描寫身體有缺陷的人物作品,如《日光流年》、《受活》、《丁莊夢》,還是講述小村落自改革開放後三十年間搖身一變成為超級大都市的《炸裂志》,都能從中感受到作家的焦慮。閻連科本人也曾在多個場合坦誠自己的焦慮,而這種「焦慮」並非指精神分析學層面的心理動態,而是在作家創作與社會互動的關係上。他曾這樣評價《受活》的意義:「對我個人來說,(小說)一是表達了勞苦人和現實社會之間緊張的關係,二是表達了作家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那種焦灼不安、無所適從的內心。」
莫言、閻連科、賈平凹,這些出生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作家,是感受到周遭的震動以及從物質到精神層面巨變的最強烈的一代人。在他們身上,既有一種與生俱來的使命感,也同時有一種壓抑以及不得不表露出來的發泄感。於是,他們在「出世」與「入世」之間猶豫徘徊:是像魯迅那樣投身於社會文化變革,還是如周作人般與現實保持距離?
對閻連科而言,就像他在獲頒「紅樓夢獎」首獎的得獎感言中說到的:「文學為卑微而存在,卑微為文學的藝術而等待。而我,是卑微的自覺的認領者。卑微,今後將是我文學的一切,也是我生活的一切。」
採訪中,閻連科向記者透露,對下一部小說,「我希望它有非常大的變化,能夠與之前的寫作作一個告別」,儘管《日熄》已經能看出一些轉變,但「我希望走的步子還能再大一些」。